为什么在医疗条件差的情况下,很多原始部落有伤害自己身体的习俗?

这是因为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是以一个经历过现代社会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的,我们因为有着最基础的现代医学知识,知道伤口如果不处理就会发脓会坏死,并且顺这个逻辑认为这种仪式习俗百害而无一利。
但首先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些有自残习俗的民族,在不同程度上也有着应对的医疗措施,比如萨摩亚人纹身时使用的露兜树树叶灰烬 + 椰子油做的药膏,利用碳酸钾与单宁酸抑菌。
埃塞俄比亚的苏尔马人,给女人撑唇盘(dhebi a tugoin),或者用燧石切割伤疤后,会使用乳香和金合欢树的树脂做药膏,利用其中的乙酸香酯和阿拉伯半乳聚糖抗炎症。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胡利人,穿刺鼻中隔佩戴饰品的时候,会将竹片刀用火烤制消毒。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然浣老师不是在吹嘘这些传统医学的神奇效果,但就如问题中所说的,即使要冒着这种风险,用这些土方法来保命也要实行这样的仪式,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些民族生活的环境条件下,这样做会带来好处。

因为这些部落民本身除了缺少医疗资源外,同时也缺少社会凝聚力和组织度,这是其在极端条件下存续至今最需要的东西。
神经人类学中,一位叫 Ronald Grinker 的学者在对刚果的俾格米人进行田野调查后,得出来了一个结论就是,青春期的疤痕仪式(scarification)所产生的集体疼痛体验,会让参与者和围观者内啡肽分泌激增从而增强群体凝聚力。
这种仪式观念就是塑造认同共识的最好机会,不光是因为仪式感,同样也是仪式造成的疤痕带来相似的外貌和体态特征,这些都会加强部落中“自己人”和“外来人”的界限划分,这就叫强化了群体边界感。
而有了内外分别,有了群体意识,那么这样最基础的组织度也就形成了,依靠这种原始的组织度,恐怖直立猿就足矣攻克许多自然界的难题,也是俾格米人能从桑加文明时代存续至今的原因。

而且许多人类学家还认为,疤痕仪式本身也是在锻炼提升疼痛阈值的一种方式,以这种悍不畏死,不惧疼痛的传统为荣,提升对疼痛的忍耐程度,也可以提升其在艰苦条件下生存的概率。
这个观点我没有太进一步研究,大家感兴趣可以自行查找。
但我觉得这玩意和一个华北地区比较熟悉的东西很像,就是天津卫混混的自残斗狠抽死签,从人类学角度上,这种当中展示敢削指头扎大腿,跳油锅大头朝下的行为,也是一种展示男性勇武的表现。
这就是自残行为,最终影响了社会身份认同的一种表现,因为 那些跳宝案子的混混,敢挨打还敢不叫疼,所以他在人类群体中的地位从无赖,变成了能吃赌场甚至是官厅米仓的存在。
对于那些条件更加艰苦的地区,这样的道理也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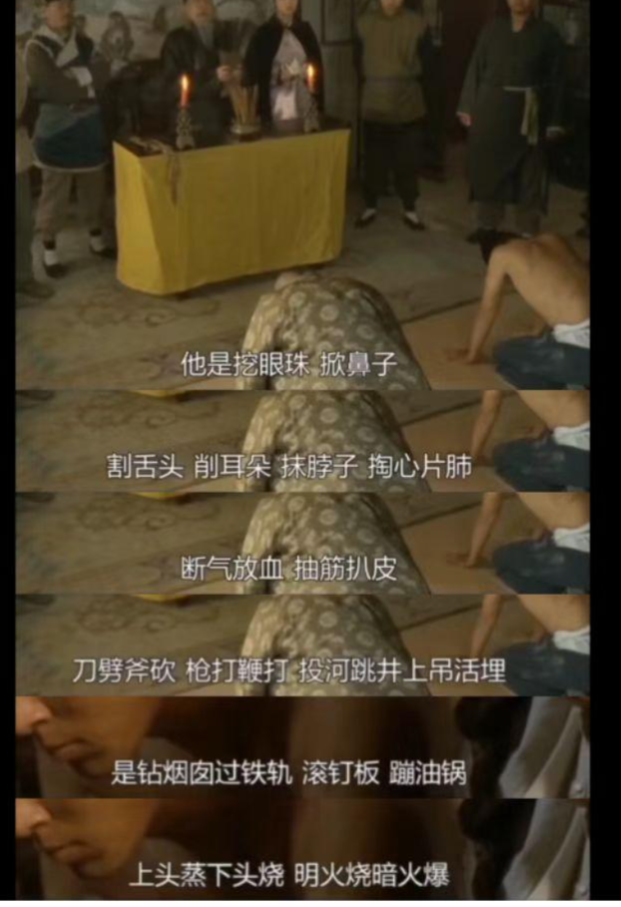
还有另一个观点认为,诸如留下伤疤、刺青、穿孔等等仪式本身是这些民族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不是所有文明都有书同文车同轨的能力,不是什么地方都有亚历山大图书馆,虽然他们可以考虑将文字刻在石头上,但还有一种思路就是刻在身上。
比如说之前提到的萨摩亚人,他们的男性传统上要求全身刺青称为“pe'a”,女性则一般手部刺青称为“malu”,而这种在身上的刺青中的几何波纹图案里,包含的信息甚至包括其祖辈相传的航海知识,而只有接受了这种刺青考验者,才被认为生理和心理都有资格参与议事。
这时候刺青一方面是仪式,另一方面也是信息载体,只不过这个录入的方式比较疼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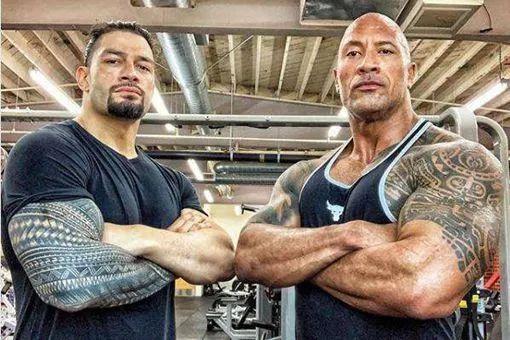
类似的还有印度北方邦的那加人,现如今许多那加族群都有着很明显的东亚面孔相貌,因为其祖上很可能是流亡跨过山脉而来的藏人。
这帮人则是拿面部刺青当击杀记录,就是因为其战士文化鼓励男性去猎头,所以每一次战争后都会填补刺青,并且将其部族迁徙、战争、盟约等等记录信息都加载在身体上。
19 世纪在英国人开始控制阿萨姆后,这些民族依然想要跟外来入侵者碰一碰,但最终还是失败,但有意思的是因为那加人在印度传统社会中同样没有融入的机会,所以其中很多人很快的改信了浸礼会等基督教信仰,并且将基督教元素也融入了其刺青当中。


所以总结一下,这种习俗在许多部落文明中存续的原因有三个,分别是提升认同感和组织度、锻炼疼痛耐受力以及作为文化传承的媒介。
而且说句题外话,人类学在历史上作为一门盛产劳保学者的学科,在很多研究中都会走向一个很社达的结论,那就是“适者生存”,之所以在一个环境中,某种我们看似不能理解的习俗会保存下来,大概率原因是这种行为更适合他们的环境。
但有意思的是,在许多文化里本来用于提升凝聚力组织度的身体穿孔,到了 70 年代开始成了一种反抗秩序,反抗组织化和规训的表现,比如说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当年性手枪乐队的经理,为了宣传朋克反抗精神,就把满大街搞身体改造的朋克仔称为“反撒切尔主义视觉炸弹”,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这里是浣熊君,一个在知乎撂地的闲散作者
苏辙嫁女“倾家荡产”,宋朝的嫁妆为何如此昂贵?为什么白人特别喜欢印度的灵修之类的概念?「剧透」从什么时候开始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