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海|不是“更正”的“订正”——从陶然纪念卞之琳文章中的信谈起

2019年3月12日,《羊城晚报》发表香港作家陶然辞世前一个月寄来的纪念诗人卞之琳的文章《当年诗人二三事》,其中提及卞之琳1992年9月15日来信中抄录的“八月二十七日写了而没有给你寄出的信”:
1980年香港一晤,匆匆已十有二年,老来事繁心烦,久疏致候,谅能见谅。年来大作时见,与盛年同登佳境,可喜可贺。《香港作家》经常收到,谢谢编委诸公垂注,今年版面扩大,面目一新,新任总编辑功不可没。不巧,就在四月十五日这一期刊登的《京华文坛三老》写我的首篇文字颇有失实处,不无小憾。作者是旧同事家的小青年,与我相知不深,似正热衷中文写作,下笔还不知轻重,文中诸多失实处,亦无非鸡毛蒜皮,本拟不予置理,奈此文一再发表,已经起了一点混淆作用,因此我想还澄清几点,以免令人误会,甚至令不甚知情的异地朋友为我作不必要的担心。考虑到用“更正”方式,清单订误,发表出来,于作者和刊物都有所不便,所以写了一篇独立性的随笔式小文,作为例证,将《老》文订正几处……
卞之琳在“大致”抄录了上信之后接着表示:
现在还是决定把文稿寄奉审阅,看可否就这样发表一下,请提意见。试加题目,长了一点。你们如能代我拟一个妥帖一点的供我选用,就更感激不尽了。不急。照片徒费篇幅,我看不要,刊出的那张是多年苍梧一行香港文友第一次来京,在聚会场合照的,显得太年轻,也合不了今日的老朽文字。
走笔至此,陶然先生评价说:“由此可见,卞老待人之诚,对当时小辈的真心客气,让我深深惭愧。”
当年无缘读到卞先生信中谈到的文稿,陶先生又是一笔带过,因而很快就淡忘了此事。近日机缘巧合,一睹《香港作家》改版号二十六期(1992年11月15日,总第四十九期)上卞之琳先生的《事实也许更有点意思》(以下简称《事实》),一连读了好几遍,结果岂止是“有点意思”,而是收获极大——此文正是上述卞先生提及的“寄奉”陶然“审阅”的文章,但未见收录进卞先生身前、身后出版的所有著作!尽管无法得知刊出文章的题目,究竟是卞先生本人“试加题目,长了一点”的呢,还是“你们如能代我拟要给妥帖一点的供我选用,就更感激不尽了”的呢,有一点毋庸置疑,虽然卞先生自称此文是“独立性的随笔小文”,实际上是写给《香港作家》编者要求订正文章失实内容的信函,如此这般,确实如陶然先生所言,是卞先生对“当时小辈的真心客气”,当然也是对刊物的客气。不过,卞先生对所谓作家纪实类文字中的“失实”变为“史实”的担心,历经三十之久,仍未过时,极富有先见之明,是研究卞先生生平史料乃至现当代作家传记史料的重要文献。虽然陶然先生也已于2019年3月9日去世,但祈望卞先生文章的手稿能被其后人妥善珍藏,有朝一日可以公开亮相。
《事实》一文的第一段,即卞之琳先生自称的“海阔天空的泛论”,谈及文人的回忆录“最不可靠”,存在刻意拔高,存心贬抑等状况。不过,文章并未从文人回忆录的不可靠或夸张深入下去,而是牵扯出一篇写他的小文章,“失实点随处都是”,让他难安缄默。此文就是发表在《香港作家》1992年改版号十八期(1992年4月15日,总第四十二期)上的《京华文坛三老》中描写卞之琳的“首篇文字”,作者为一个小青年,是“朋友家的孩子”、 “和我并不相熟”,“有写作才份的,只是目前显然没有抵挡得了时髦的不正趣味的诱惑”。
卞之琳先生在《事实》一文中指出:
就写我的这篇文字而论,首先错把我这个生活中并无光彩的平凡人物硬充舞台上的显眼角色,无意中诉诸扭曲、颠倒、“创造”、以假乱真的手法,文中写到的是有些真实的,例如我在他索赠书上写的两行字和请他读序的一句话,他借此发挥评论,也有点意思。我理解人家是“做”文章,倒是想抬举我,殊不知我偏不配“做”戏,至少目前还进不了派给我的角色。文章中失实点随处都是,虽然都是鸡毛蒜皮,无关宏旨,但是在作为纪实的文章中绘声绘影了,传开去,传下去,自会有好事的文史研究者坐享现成搜罗去,再七嘴八舌,重复三遍两遍,也就成了铁打的“史实”。
卞之琳先生自称平凡人物,不愿作舞台上的显眼角色,自然是谦词。他原本以为,失实“这种溃斑,是要经过些时日才会积久到洗刷不净的,且不去计较也罢,既免得像太珍惜自己的渺小形象,也免得挫伤年轻人文艺习作的积极性”,但问题在于,《京城文坛三老》这篇文章,“一再发表”——此前已见于北京出版的杂志,卞先生曾就失实部分向作者“提过口头抗议”,遗憾的是,作者略加修改后,又把文章投寄到了《香港作家》。对此,卞先生摆出事实,对“妙文”的“妙笔”作了回答:
现在他还是不忍割舍这篇“妙文”的多少“妙笔”。出言还不知轻重,不自知其为恶俗不堪的污蔑语中有一句算改了,否定了原来文中所横加我的笑柄——紧接“大跃进”的“三年困难时期”捡别人扔掉的香烟头过瘾——说是误听了张冠李戴的谣传(实际上我们文化界还没有谁寒伧到这地步,招惹过这个谣传,恐怕是作者谦让了自己的发明权。)作者在文中还继续让我说口头戒了烟却还是没有戒掉,还笑我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一见别人拿出好烟来,就破戒大抽!我也不需他替我谦虚说平时只买便宜烟,我还不至于穷酸绝顶,“文化大革命”以前,我还和许多文化人一样,同被划入过并不相称的“三名三高”的行列,也算戴过这顶歪帽子,并不光荣,倒也享受过一点实惠。就在这三年困难来临的时候,我充分利用每月发给的两张优惠券,去供应站买两条当时算最贵的“大中华”,还借用邻居同事一位不吸烟的大学问家的那两张券去加买两条。在以前以后,在海内海外,我一直不买烟则已,买起来还相当挑剔。如今我辈“臭老九”当然更无从攀比“个体户”新贵了,幸而不少人如我,早已根本不理会香烟了。
卞先生罗列的事实,不必多做解释。只是其中“三名三高”一词,年轻一代可能比较隔膜。《当代中国流行语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 , 1982年8月版)的解释是:“即名作家、名演员、名导演、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文革”是由文艺界开始,而文艺界最早批的就是三名三高人物。如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就因系三名三高人物而被迫害致死。此词主要流行于1966年至1968年。”这个词语源起可能更早,大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卞之琳文中称自己“文革”前被划入“三名三高”行列吻合。
对《京华文坛三老》的失实之处,卞之琳先生提出,“我虽然不必去全面订正,还是得澄清几点,而这类事实本身大致比求趣虚构还更有意思一点”。
《事实》一文中对《京华文坛三老》中失实文字的订正,除了上述所引文字外,还有文章弄错了卞先生的住址“令人怀疑我搬了家”、以及戒烟未获成功等多处,恕不一一引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事实》一文细读。
拙文在收尾之前,尚有几个关键之处还需要费点笔墨,这也是我十来年养成的史料癖和考据癖的习惯使然:卞先生给陶然先生的信及《事实》一文,无论提及失实的文章是“一再发表”“最初见于北京出版的杂志”,还是谈及作者是“旧同事家的小青年”“朋友家的孩子”,均未点出具体名称,这当然是卞先生的宅心仁厚和对晚辈的客气。我本来也应该遵循卞先生的客气,对此不予深究的,不过,因为有所发现,深感老人家的客气是不应当作福气的,因此,不揣鄙陋,只提供下面几个事实供读者去参考。
卞先生在给陶然去信之前,曾在1992年7月22日晚给广东《华夏诗报》主编写有一信,刊登在《华夏诗报》1992年第7期上,后转载于《香港作家》改版号二十五期(1992年10月15日,总第四十八期),题目为《补趣》,内容同样涉及上述失实文章。从信的内容推断,应该是《华夏诗报》主编看到《香港作家》刊登的《京华文坛三老》一文后,想加以转载而给卞之琳去信,结果,卞先生迅速回信“赶快建议你们不要转载”。这封信透露失实文章初刊北京的杂志,名为《中华儿女》(双月刊),作者为“龙冬”。卞先生在信中说:
龙冬这孩子当然是聪明、善良的,将来也可能是写文章的能手。目前却像多少沾染了时髦的低级趣味,为文爱耍花招,不够认真。他最近在《香港作家》上发表的有关我的那段文宇,我早就在内地出版的繁简两种字体版的《中华儿女》这个刊物上见过。我了解他对是我(“对是我”疑似“对我是”之排版错误——海注)尊敬的,但是弄巧成拙,我曾当面向他抗议,指出过许多失实以至无中生有的捏造。后来好像在以后出的一期上改正了。现见《香港作家》第19期上,他只改了自以为最有趣、而不知道是最侮辱人的、不知从何处捡拾来的诽谤话,说我在“三年困难”期间,捡人家丢掉的烟蒂头来吸。他承认是根据张冠李戴的传闻,还有多处与事实不符或正相反的地方,说我住“史家胡同”,即是一例(这本来无关紧要,但己害得你们怀疑本来写的正确的地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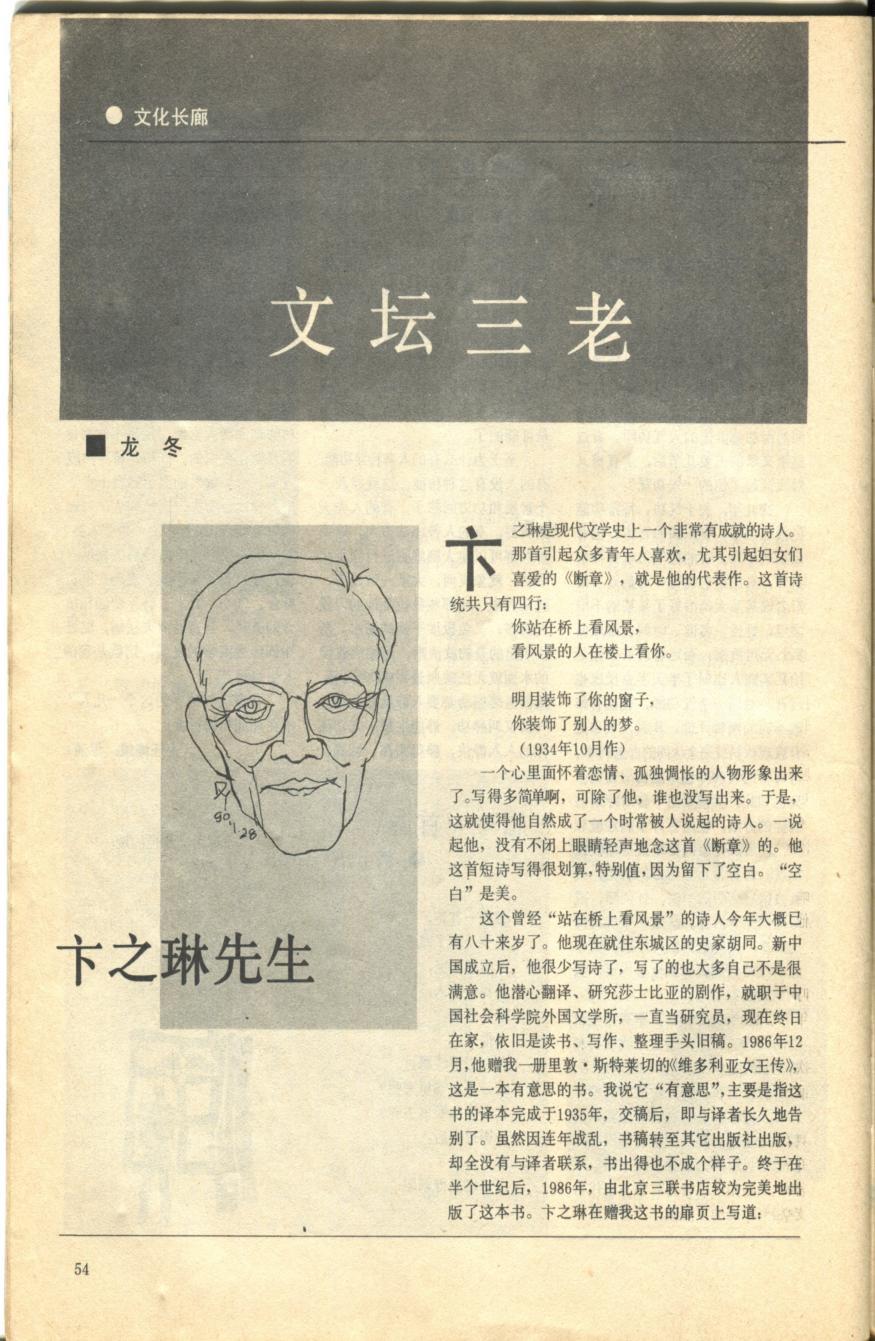
查询《中华儿女》,1990年第3期“文化长廊”栏目上确有署名“龙冬”的文章《文坛三老》。继续在网络上搜寻,原来“龙冬”是熊耀冬的笔名(其父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算是卞之琳的同事),1999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曾在多家出版社任职,2017年辞去公职,迄今已出版著作多种。再回头查看,《中华儿女》1990年第3期扉页的编辑名单里,有“熊耀冬”的名字,当期刊物中也有数篇熊耀冬担任“责任编辑”的文章。
《文坛三老》之“卞之琳先生”部分,卞先生文中提及的“原来文中所横加我的笑柄”的文字,以“据说”开头:
据说有人亲眼见到他在三年困难时期,在一个汽车站弯腰捡起地上的一节烟屁股,我不敢相信这个传说,也许是那人当时没看清楚。可他是对香烟比较喜好的。
很抱歉,限于网络等条件,我至今无缘看到《香港作家》刊载的《京华文坛三老》原文,不知道卞先生所言“恶俗不堪的污蔑语中有一句算改了”的具体情形。不过,偶尔浏览“豆瓣”,发现有署名“龙冬”的网民发布于2019年2月25日、写于“1990年元旦”的旧作《卞之琳先生》(链接:https://www.douban.com/note/708159011/?_i=32978623aN1YHw),有这么一句话:
据说有人亲眼见到他在三年困难时期捡烟屁股,后来才知道,这大概是一个张冠李戴的传说。但他过去对香烟的喜好,却是特别的。
这句话,大概就是经卞之琳先生抗议后再度发表的《京华文坛三老》中有关卞先生的相关部分所作修改的文字。既然已经知道“据说”的内容是张冠李戴的传说,却依然“不忍割舍这篇“妙文”中的“妙笔”,甚至在“张冠李戴”之前还要加上“大概”这个模糊不清的定语。岂不闻“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的古训。难怪卞先生在《故事》中会无奈地指出“是作者谦让了自己的发明权”“出言还不知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