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蓝评《记者加缪》|在流放地与王国之间

《记者加缪》,[法]玛丽亚·桑托斯-赛恩斯著,张冬锐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24年10月出版,324页,79.00元
2024年11月23日,为纪念斯特拉斯堡解放八十周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宫发表演讲,并宣布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入祀先贤祠。布洛赫的杰出贡献与高尚人格自然无可争议,但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制造”一个历史事件,马克龙的用意也显而易见:在演讲中,马克龙称布洛赫是“影子军队中的启蒙者”(l'homme des Lumières dans l'armée des ombres);而这位投身抵抗运动的历史学家最终惨遭盖世太保杀害的命运,使得围绕他足以形成一个“哀悼传统”(卡内蒂语),进而凝聚越发涣散的人心。值得注意的是马克龙对于二战时期阿尔萨斯及摩泽尔地区“非己所愿者”(Malgré-nous)的强调:“纳粹德国强行征召我们阿尔萨斯和摩泽尔地区的年轻人入伍,把他们当作帝国的孩子,尽管他们是法国的孩子……他们的悲剧必须被赋名、承认和铭记,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尽管并不知道“非己所愿者”的真实愿望,但凝聚共识是我们乐见的历史使用方法,布洛赫的家人也欣然接受了这一荣誉(布洛赫的孙女叙泽特·布洛赫表示对此“非常自豪,非常感动”)。但也有人做出了不同的决定。2009年,法国时任总统萨科齐希望在阿尔贝·加缪去世五十周年之际,将其灵柩迁入先贤祠,却因其子女的强烈反对未能成行。“我认为加缪并不需要萨科齐的肯定,”加缪的传记作者奥利维耶·托德表示,“倒是萨科齐更需要一些知识分子的光环来装点门面。”
我们无需对当事人的决定予以评判。人因其立场而真实,而值得捍卫的自由之一便是决定自己持有何种立场。在新闻学专家,同时也是加缪研究学会会员的学者玛丽亚·桑托斯-赛恩斯的著作《记者加缪》当中,我们看到的既是一个“非常规”的加缪,更是一个以今天的观点看来“不够客观”的记者。“加缪将记者定义为‘首先应该具有思想的人’。这一概念有别于盎格鲁-撒克逊新闻模式,后者建立在以客观性为基础的职业价值体系之上。”(248页,引用时有改动)记者加缪持有的原则是“客观并非中立”,记者必须形成自己的判断,并对这一判断负责。尽管作者通过转引加缪在新闻界的“战友”让·达尼埃尔的观察,一再强调对加缪而言,“新闻工作不是流放地,而是天堂”(161、164页),但由于个人判断与现实本身的局限,加缪的新闻工作远未抵达天堂之境——这种不可即基本上是他最终退出新闻界的主要理由——但我们仍有理由认为记者加缪是幸福的,正如他本人对西绪福斯的看法。
阿尔及尔一年:四次战斗,两胜两败
加缪的记者生涯起步于阿尔及尔本土报纸《阿尔及尔共和报》。“加缪成为记者时只有二十五岁,但他那时已经具备了天赋、正直和成熟,这些品质引导他去谴责不公正和苦难。”(85页)前一年加缪的工作是在阿尔及尔气象研究所担任办事员。对于一个因身体原因无法成为哲学教师、已经待业两年的哲学系毕业生而言,这份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考虑到这份工作可以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创作,它与加缪最初的职业愿景相去不远。然而与帕斯卡尔·皮亚的相遇改变了一切。“(与他相处会带来)男人之间会有的那种乐趣。那种很微妙的,只是借火或帮对方点烟的动作——某种默契……”(《加缪手记:第一卷》,黄馨慧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124页)两人在意欲进军新闻业的理想主义者让-皮埃尔·弗尔招揽人马的过程中相识。很快,原本在巴黎《今晚报》任职的皮亚成了这份外省报纸的实际领导者,而加缪则辞去了气象站的工作,开始担任通讯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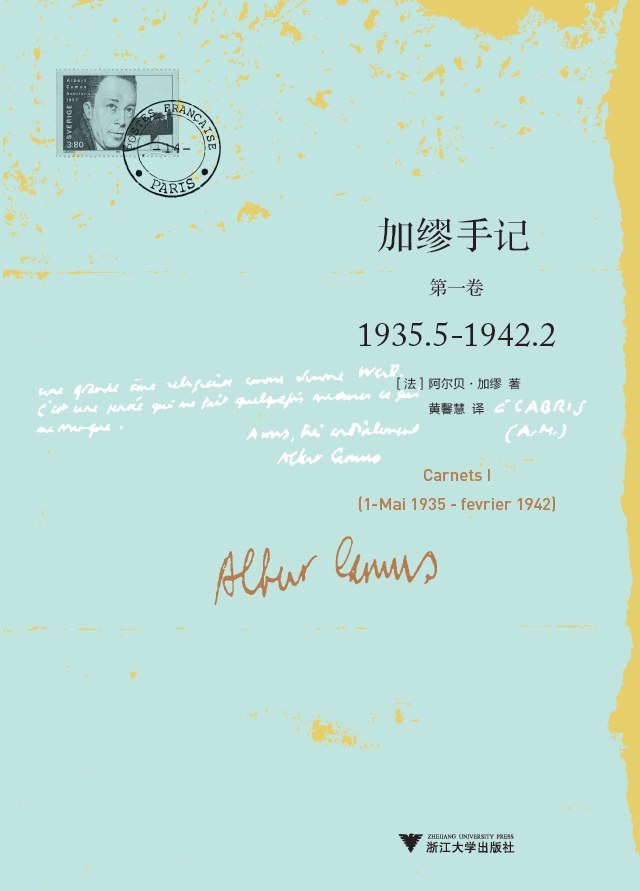
《加缪手记:第一卷》
用狄更斯的经典套话来形容《阿尔及尔共和报》所面对的时代环境似乎极为贴切,“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作为一份打算“与一切斗争并肩作战”的报纸,“《阿尔及尔共和报》问世的时间非常好:此前几天的9月30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签署了《慕尼黑协定》”([法]奥利维耶·托德:《加缪传》,黄晞耘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164页),然而单靠讨论国际形势无法吸引读者兴趣,国内新闻的报道权限又势必因时局阴影下当局的越发敏感不断缩紧。但加缪无暇考虑这些。成为记者、肩负起“报道者”的责任,意味着他终于可以让他所关切的苦难公之于世——他自己正是从贝尔库的贫民窟而来。于是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存续的短短一年时间里,加缪完成了五十余篇文章,其中甚至包括四组针对现实事件的系列报道。

奥利维耶·托德著《加缪传》
加缪的第一次跟踪报道,针对的是发生于1938年的“奥当案”。皮埃尔·奥当原本是特雷泽尔镇一家农业互助社的普通职员。出于对当地弱势农民的同情,奥当提前从他们手中收购了当年的小麦,以规避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然而此举却触动了当地富农及上层殖民者的利益。在尚未展开调查的情况下,奥当便被当局以私自囤积小麦的罪名关进了监狱。奥当给《阿尔及尔共和报》写信描述了自己的状况,读到这封信的加缪立刻投入到“战斗”当中。因为“对他而言,奥当是阿尔及利亚不公正现象的象征,在这里,强者的法律占主导地位,那是有权有势者的法律”(97页)。尽管当时为奥当案奔走呼告的记者不止加缪一人,但他的深入调查与雄辩风格超越了事件本身,将讨论上升到人性层面:“在一个苦难和荒谬导致许多人失去人性的世界里,拯救一个人就等于拯救了自己,也等于部分拯救了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的人类未来。”(98页)更关键的举动则是他在调查伊始即在报纸头版发表了一篇写给当时阿尔及利亚总督的公开信,谴责当执法官程序不当、滥用权力。在赛恩斯看来,加缪此举承袭了自左拉乃至伏尔泰以来法国知识分子通过新闻介入现实的传统:
在报纸上发表致国家总统或国家高级官员的公开信,这种新闻体裁是法国新闻界牢固传统的一部分。在更早的时候,法国新闻史上的另一著名事件催生了巨大反响:由伏尔泰揭发的卡拉斯事件在舆论场上以公开信的形式向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或国家高级权力机构提出质询,这一行为至今仍然存在,但仅出现在极其特殊的事件上。加缪当时是一名年轻记者,他采用了这一传统形式,其他常在报刊专栏发表文章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比如左拉(他也是一名记者)和伏尔泰(他也是报纸的长期撰稿人)。简而言之,这是在极端情况下,第四权向第一权发出的呼吁,要求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件伸张正义,并因此动员公众舆论。(102页)
案件的最终结果,宣告初出茅庐的记者加缪几乎大获全胜——奥当被当庭宣判无罪。尽管《阿尔及尔共和报》因此成为当局的眼中钉,为日后的停刊埋下伏笔,但加缪很快投入到第二场战斗中。这次陷入麻烦的是当地进步主义宗教领袖奥克比,他被指控谋杀了当地保守派宗教领袖卡乌勒。这宗政治色彩浓厚的谋杀线索错综复杂,但加缪一开始便坚定地站在奥克比一边,因为他坚信一个持有包容、温和立场的知识分子,绝不可能诉诸谋杀这样极端的手段,“加缪把赌注押在一个他认为正派的人的清白上”(109页)。在围绕这一案件的系列文章中,加缪将奥克比的形象与反殖民斗争联系在一起,而奥克比最终被无罪释放,似乎意味着他再下一城。然而这场胜利却远不像奥当案那样痛快,“让加缪感到不自在的是,被告方的几名证人,鲁弗拉尼、塞勒、高兹朗、马卡西这几位先生都是《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董事会成员”(托德《加缪传》,175页)。而多年后浮出水面线索,也暗示了奥克比并非完全清白,加缪的辩护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免于牢狱之灾,却也导致他作为斗争领袖生涯的终结(参见[美]赫伯特·洛特曼:《加缪传》,肖云上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269-27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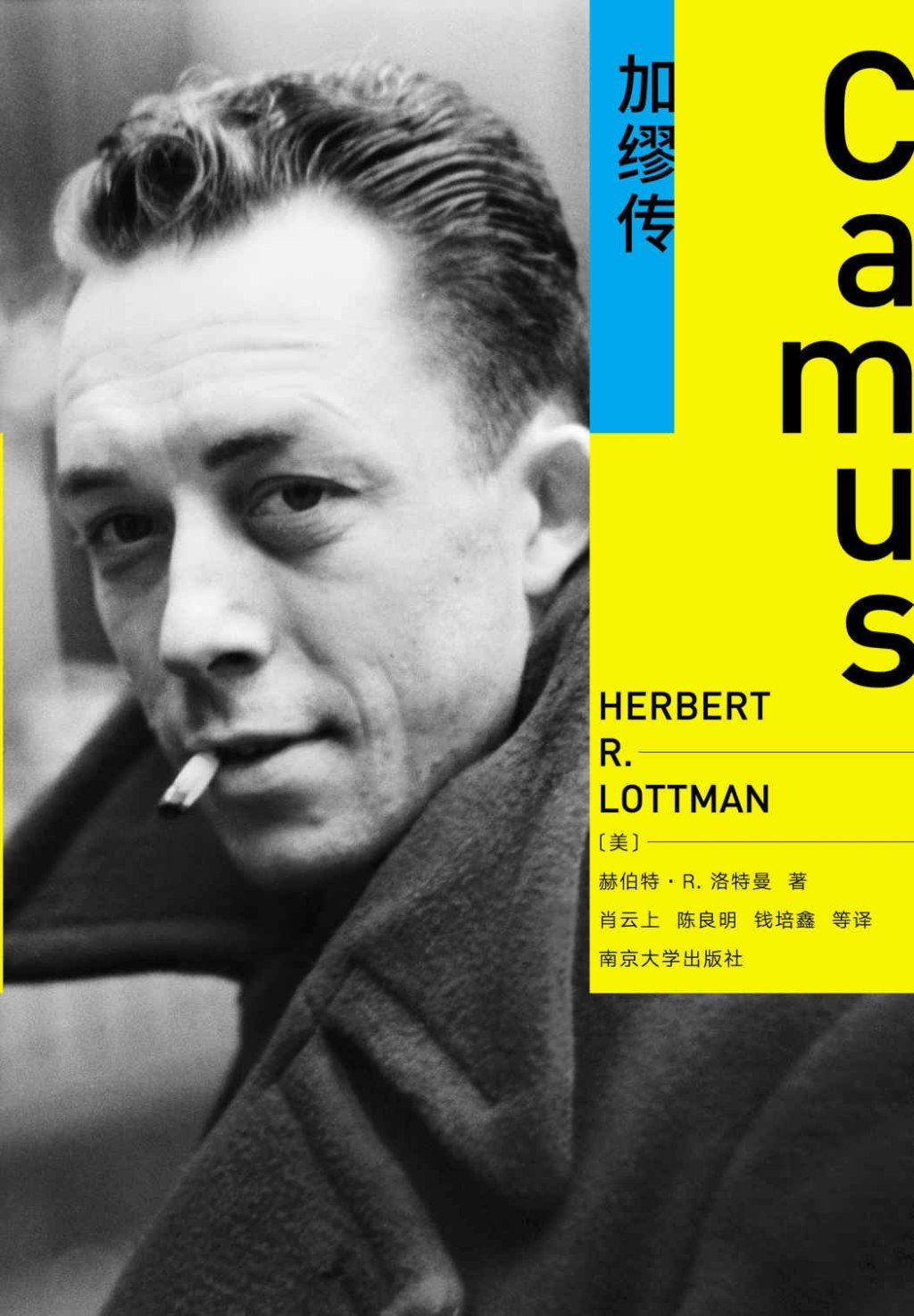
赫伯特·洛特曼著《加缪传》
也许正是因为奥克比事件中高层斗争的暧昧不明,让加缪决定更加专注于为底层苦难发声。他的第三场战斗涉及的是“欧里博纵火案”。一群阿拉伯农场工人向雇主要求涨薪,雇主不得已答应了他们的要求,随后却指控他们在示威结束后纵火焚烧了“建筑物”——实际上只是一些稻草棚。加缪立即抓住其中破绽,“指出工人获得了他们要求的微薄涨薪后再进行纵火的荒谬性。工人们的反抗已经在地主示意压制的一个小手势之后被扑灭了”(113页)。加缪继续沿用他的“辩护”策略,试图通过要求公布工人们的真实薪资状况唤起大众同情。然而这次的舆论战未能奏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次审判还是被用来作为一种威慑,以防止进一步的叛乱”(同上)。涉案工人最终被判十二个月的苦役,“1939年7月30日,加缪发表了他关于此案的最后一篇文章,阐述了被剥夺唯一家庭收入来源对于被判刑的农场工人家庭意味着什么”(115页)。而对欧里博纵火案的关注、对苦难的描述与想象,则直接催生了加缪在《阿尔及尔共和报》最后一组专题文章“卡比利亚的苦难”,而这也是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发表的文章中,日后唯一被他选入文集的作品:
有人会说:“请小心,外国人会抓住这一点不放的。”然而,如果真有人会抓住这一点不放,那么他们就已经在世人面前以其厚颜无耻和凶暴残忍受到裁判了。如果法国能够奋起而自卫,反对他们的话,那手段可以用大炮,也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即我们仍然能讲出自己的想法,仍然能以我们每个人的绵薄之力来纠正不公正的做法。
我所起的作用绝非去追寻什么虚幻的责任,我没有当一个控诉人的兴趣。即使我有这种嗜好,也还有许多许多其他的事不允许我那样去做。一方面,我非常清楚,经济危机已经给卡比利亚带来了灾难,不能再让它遭受损害了。另一方面,我同样也非常清楚,这种开明首创精神会遇到多大的阻力,有时这种阻力是来自最上层。最后,我也非常清楚,一种愿望,不管其原则有多么完美,在执行过程中是会走样的。(《加缪全集:散文卷II》,王殿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32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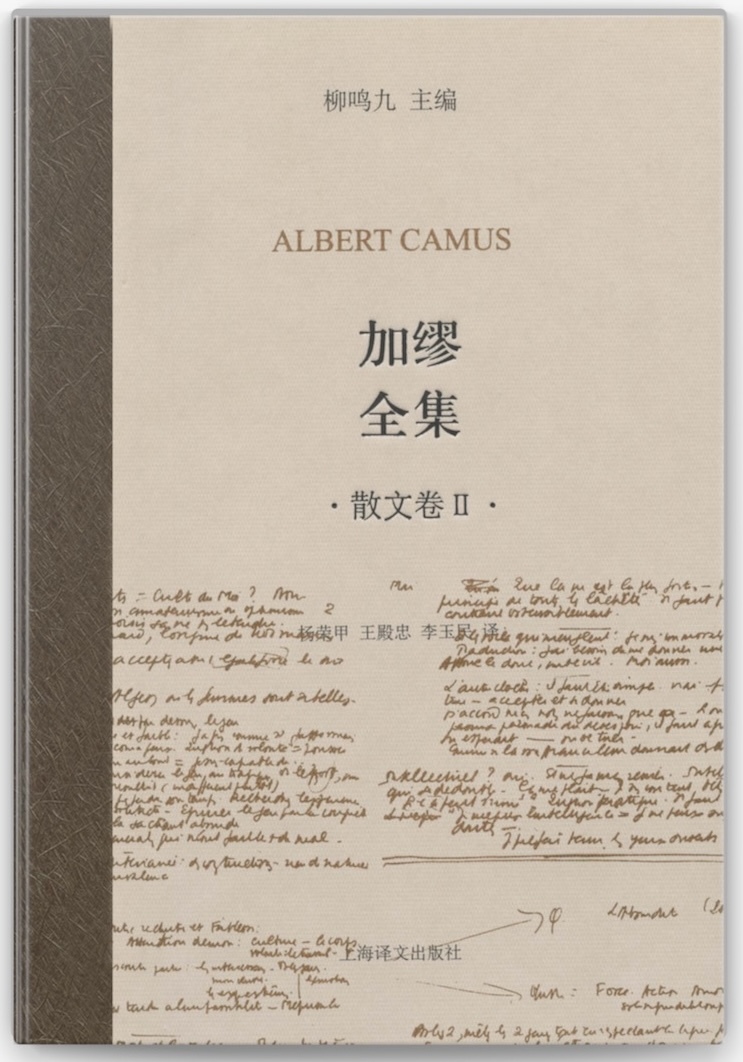
《加缪全集:散文卷II》
不难看出,到这一组文章,加缪已经开始从记者转向一名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从一名阿尔及利亚记者,转变为一名法国作家。日后他将会被不断诟病抛弃了自己的出身,但早在二十六岁时,他便已经遇见了自己与现实难分胜负的僵持局面。现实将反复冲毁理想主义者的沙堡,但反抗的痕迹终会留下。
“抵抗”在地下:反对恶之根
《阿尔及尔共和报》最终在1940年1月宣告停刊,加缪也成了“在阿尔及尔不受欢迎的人”(43页),不得不离开故土另觅机会。他先是在奥兰定居,随后拜皮亚所赐,谋得《巴黎晚报》的校对工作。然而很快,如让·达尼埃尔所言,“加缪比其他人更容易被赋予一项使命”(269页),1943年,加缪加入抵抗运动,地下报刊《战斗报》成为其反抗纳粹的主阵地。关于这段“不可战胜的夏天”的经历,先前提到的两种加缪传记及美国生物学家西恩·B. 卡罗尔为加缪与科学家雅克·莫诺撰写的双人传记《勇敢的天才》(孙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等作品均有详细叙述。赛恩斯主要从“新闻冒险”的角度展开考察。在她看来,《战斗报》时期的记者加缪延续了他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工作时养成的习惯,“对于语言和表达的准确性十分严格,对为了服务于真相和有价值的信息所采用的语调也很苛刻”(165页)。更重要的是,选择通过社论表达主张的加缪依然坚持立场先行,“求索真相往往意味着选择立场……由于行动与作品、新闻与文学之间的完美共生,特别是他的编辑工作,加缪进入了新闻史”(165-16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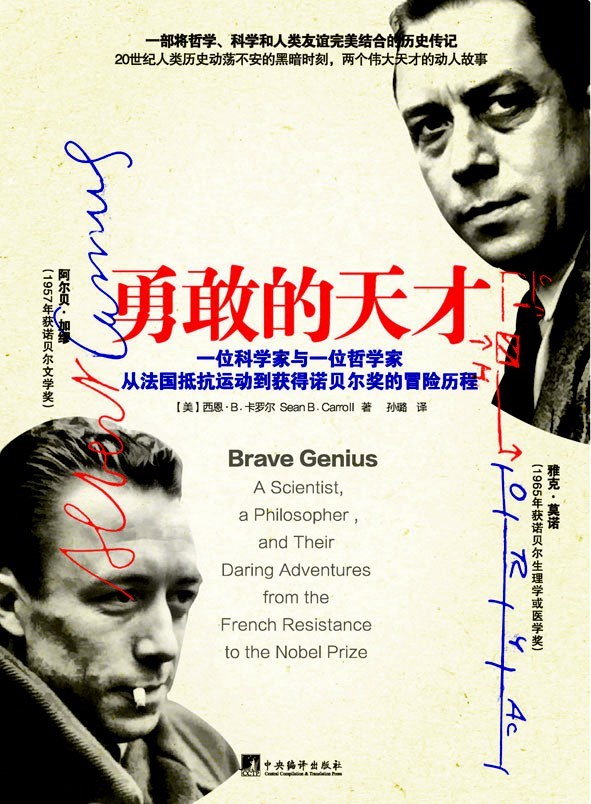
西恩·B. 卡罗尔著《勇敢的天才:从法国抵抗运动到获得诺贝尔奖的冒险历程》
《战斗报》的冒险为加缪赢得了某种权威。在巴黎沦陷的黑暗时光里,加缪俨然成为读者的精神支柱。“1944年12月,读者们简直要从报摊上抢《战斗报》,人们如饥似渴地读加缪的社论,整个巴黎都在谈论它。”(167页)1950年,加缪选编自己这一时期的专栏文章结集出版,他在前言中写道:“本书概括了一位作家投身本国公众生活四年间的体验,这一体验,很自然地以丢掉了某些幻想和更坚定了信心而告终……即使仅剩下了一个人,只要朴实无华的真理原原本本地被接受,那么希望也就同时存在。”(《加缪全集:散文集II》,29页)
“戴高乐将军第一次执政结束后一个月,我进了《战斗报》,它是当时巴黎文坛最负盛名的报刊。阿尔贝·加缪写的社论声誉鹊起:此乃一个真正的作家在评论时事。”(《雷蒙·阿隆回忆录》,杨祖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297页)雷蒙·阿隆的回忆不仅佐证了加缪通过《战斗报》的“战斗”取得了巨大声望,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他更倾向于将加缪视为“真正的作家”,而非新闻业从业者——一位作家高度介入现实并非一件寻常之事,当他抛弃“虚构”之屏障直接向公众分享自己的信念,也意味着他需要承受这些信念对自己的直接拷问。对此托尼·朱特的评价更加切中肯綮:“加缪的观点在抵抗运动的一代面临第四共和国的两难和遗憾之时,为他们定下了道德基调,他的许多读者‘业已形成了每天通过他来思考的习惯’。到了五十年代末期,他感到和自己的公共自我已经发生了分裂,这也成了加缪作品和演讲中持续焦虑的来源。”([美]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章乐天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12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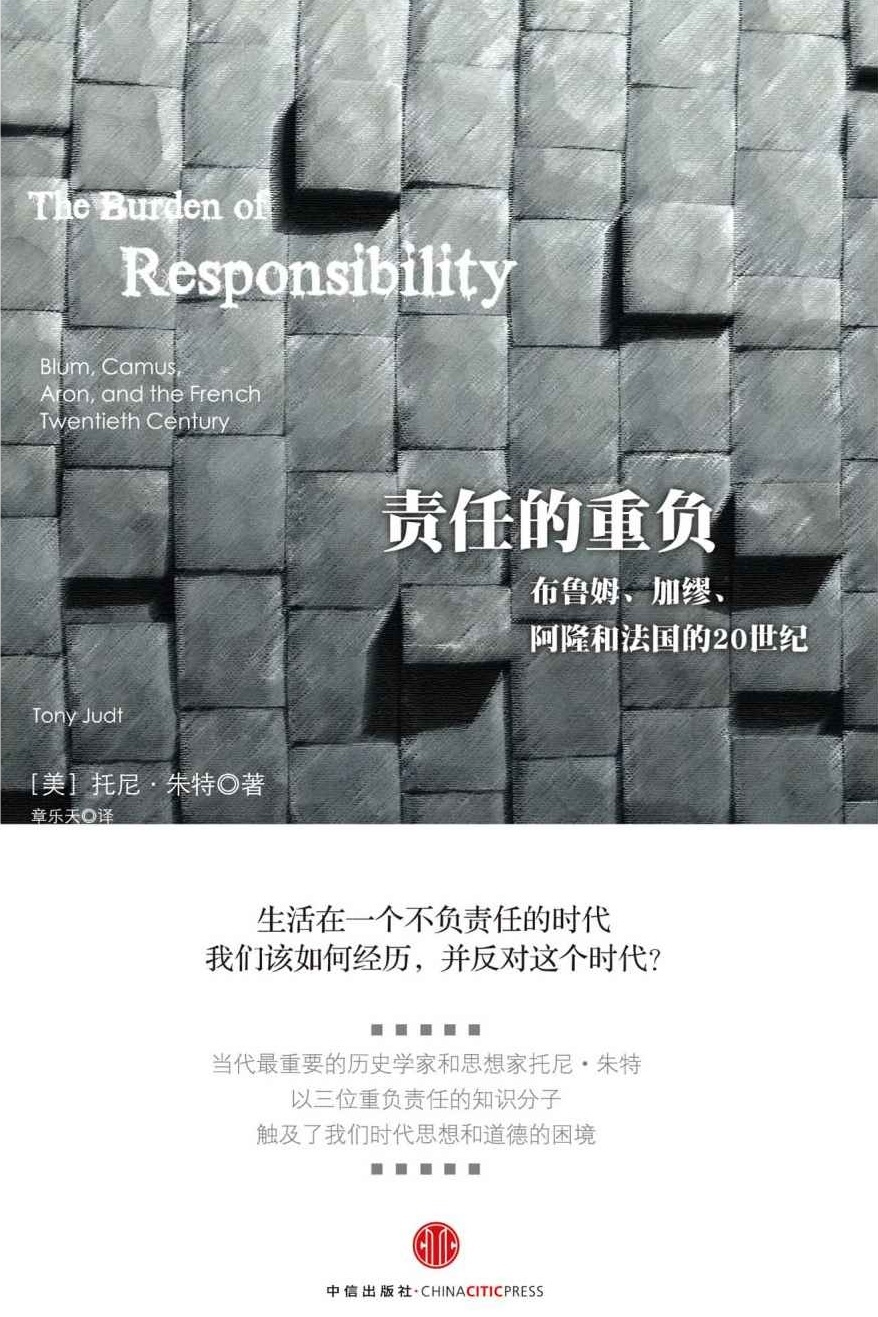
托尼·朱特著《责任的重负》
无论如何,与阿尔及尔时期一样,加缪仍有时间享受自己的胜利果实。1944年巴黎解放,意味着记者加缪可以从“地下”抽身。他很快又回到了自己在《阿尔及尔共和报》时期经营的主题。1945年他再次回到卡比利亚,随后在《战斗报》上发表了六篇基于实地考察完成的文章。但相比于几年前面对苦难的单纯发声,如今的加缪必须做出抉择,因为“在法国纪念解放的同时,阿尔及利亚在进行殖民镇压”(179页)。一如既往,在这组报道最后,加缪仍在呼吁和平与正义——依然是以更接近一名法国作家的姿态:
今天的世界充满了来自各处的仇恨。到处都是暴力和武力、屠杀和叫嚣,污染了人们本来认为已经远离了骇人毒气的空气。为了反对仇恨,我们必须去做我们能为法国以及全人类的真理所做的一切。(183-184页)
“如此我们在他人面前便得以自由”
作为一名“偶像级”作家,议论、研究加缪者历来众多。新闻学专家与加缪研究者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得赛恩斯更倾向于将这位偶像引入如今因“后真相”“信息茧房”等时代症候而越发疲软的新闻事业当中。“对新闻业的反思,是加缪留给我们的最美丽、最正义的遗产之一……通过提升语言水平来提升这个国家。这是一场挑战……以记忆对抗遗忘,以不敬对抗服从,以自由对抗奴役。这是对加缪所捍卫的新闻业具有的颠覆性意义的忠实诠释。”(246页)这一结论自然正确且振奋人心——如今我们实在太过需要加缪式的勇气与乐观精神,来对抗维勒贝克式的虚无与“屈服”。但作为一部试图提供开创性意义的作品,赛恩斯依赖的材料过于单一:全书反复引用让·达尼埃尔和罗歇·格勒尼耶两位加缪在新闻业的“战友”的观点,在构成作品主体的同时还依赖二人的言论对更普遍的观点,即加缪对新闻业其实兴趣不大加以反驳。即便两人的回忆足够可靠、观点足够有力,这样的写法还是使得作品本身过于单调,而这种单调导致了赛恩斯始终未能直面“记者加缪”职业生涯的关键问题,即他缘何并未抵达“王国”,反而以一部《堕落》宣告了自己的退场。
匈牙利裔加拿大学者埃丽卡·戈特利布处理了相似的难题——她的作品名字便叫作“奥威尔难题”。这部作品讨论的是“奥威尔绝望”,即有观点认为奥威尔是因为绝望才写下了《一九八四》——作品的根本意图是否定人类为自由斗争的价值。经由将《一九八四》投入“讽刺作品”“奥威尔的创作谱系”“心理学理论”三个语境进行的交叉论证,戈特利布最终得出结论:“敢于为个体独特性和解放受压迫者挺身而出;敢于坚持高尚的道德行为,哪怕不能立即得到可衡量成效的结果;敢于坚守我们最重要的人类遗产——未被败坏的意识和话语;这是与奥威尔对人类精神的信念不可分割的斗争本质。”([加]埃丽卡·戈特利布:《奥威尔难题》,陈毓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420页)值得注意的是戈特利布也在这部作品中谈到了加缪,“加缪的奥兰城,我们看到即便是在老鼠出现之前,它就已经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它被阻隔在精神生活的源头活水之外,成了荒原,成了地狱”(同上,291页)。固然戈特利布在这里讨论的是“小说家加缪”的经典文本《鼠疫》,但《鼠疫》中不乏对新闻业的批判——若是能将“记者加缪”的现实遭遇与文本中的创造结合起来进行论述,我们或许会得到一个更具说服力的知识分子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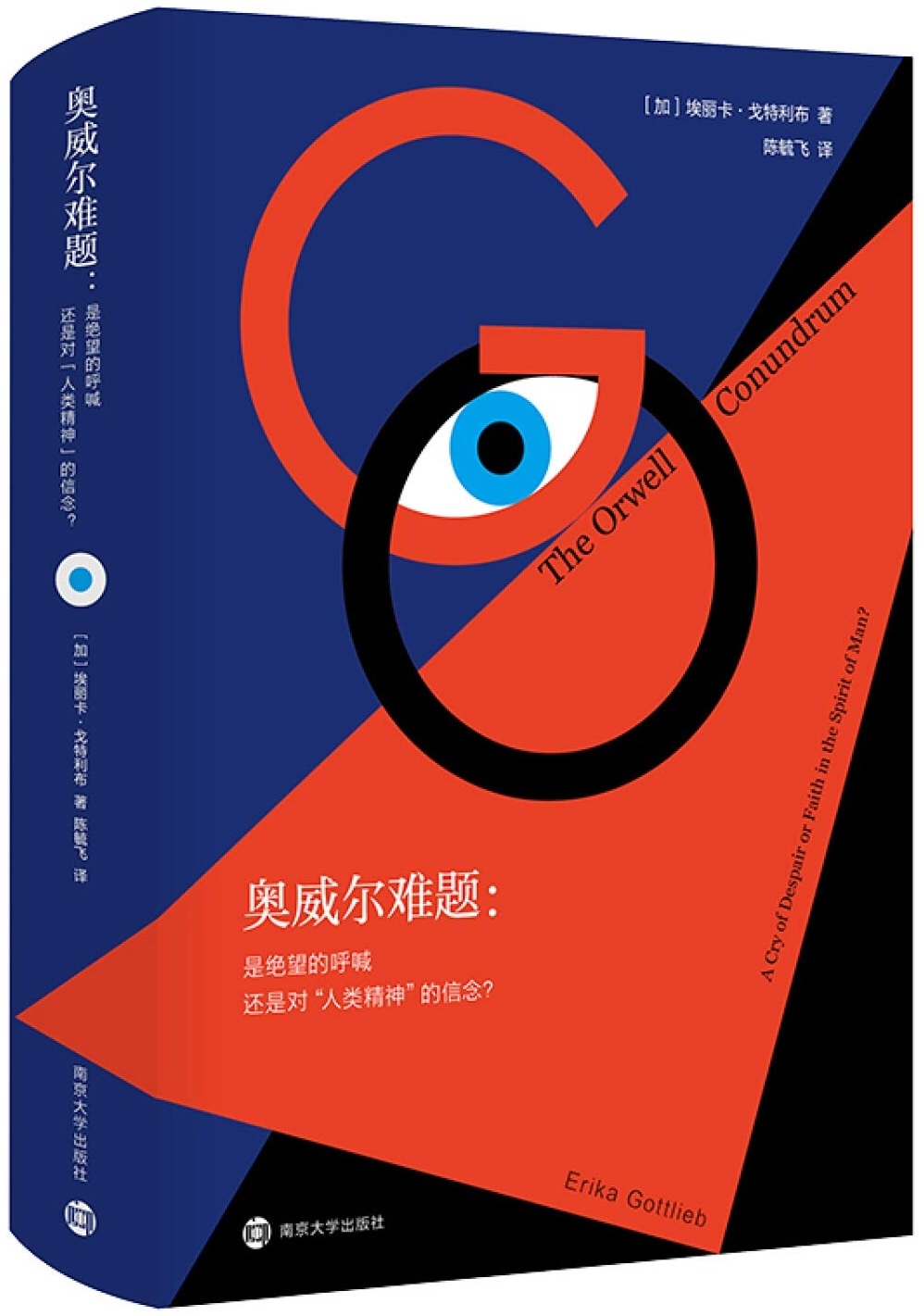
埃丽卡·戈特利布著《奥威尔难题》
另外值得关注的“难题”,则是加缪作为一种知识分子代表,其声誉的持续走低——这一趋势甚至从他生前摘下诺贝尔奖便已开始。根本问题也许还是加缪试图在正义与自由之间寻求平衡的策略,这使得他既是上位者眼中的“麻烦”,同时也无法取得弱势者的信任,甚至招致他们的“反抗”。2015年阿尔及利亚作家卡迈勒·达乌德凭借《默尔索案调查》一书获龚古尔奖首奖,这部以“为在《局外人》中被默尔索谋杀的阿拉伯人赋名”为己任的作品的成功,可以看作是“反加缪”者的一次胜利。然而到2016年,达乌德便因为针对德国跨年夜性侵事件的评论——“在阿拉伯世界中存在一种对于女性、身体及情欲的恶劣对待”——遭到十九位学者联名发文抨击,他们指责达乌德重演了“东方主义式最扭曲、最具成见的陈腔滥调”(据维基百科“卡迈勒·达乌德”词条)。到2024年,达乌德再次凭借《天国美人》一书摘下龚古尔奖,而这次只过了几个月,他便再次陷入争议漩涡:此书以阿尔及利亚内战为主题,然而很快便有一名内战幸存者指控达乌德盗用了她的个人经历与创伤。由于达乌德的妻子是一名精神治疗师,同时的确为这名幸存者提供过治疗,后者的指控似乎并非空穴来风。这一事件因为同时涉及写作伦理、医疗伦理,乃至民族问题而变得无比复杂——当年致力于反抗加缪让阿尔及利亚受害者无名就戮的达乌德或许很难想到,自己的作品如今可以在法语世界得到认可,却被禁止以阿拉伯文在阿尔及利亚流传。

施罗默·桑德著《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
加缪及其反对者“俄罗斯套娃”式的命运,似乎预示着知识分子介入现实这一伟大传统,其合法性正在被不断削弱。“如今,我们可能正处于某个已知文明的终点,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外观神秘的时代……对前国家神话的强烈渴望正处在最高峰。……将要面对未来冲突的知识分子将不同于巴黎曾经那些伟大的开路者——在过去漫长的世纪里他们曾是我们的指南针。”([以]施罗默·桑德:《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樊艳梅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215页)然而无论是否被信赖,指南针终究存在。哪怕我们仅仅将记者加缪的尝试看作天真到“荒谬”的理想主义,我们也不应忘记作家加缪针对个人生活,尤其是生活在荒谬世界的个人的建议:“能够和荒谬分庭抗礼的是一群向它挑战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为这群人效力,就是矢志为对抗一切谎言或沉默的政治而展开对话,直到荒谬的程度。如此我们在他人面前便得以自由。”(《加缪手记:第二卷》,黄馨慧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168页,引用时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