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以宏观历史研究意识……重塑中国绘画史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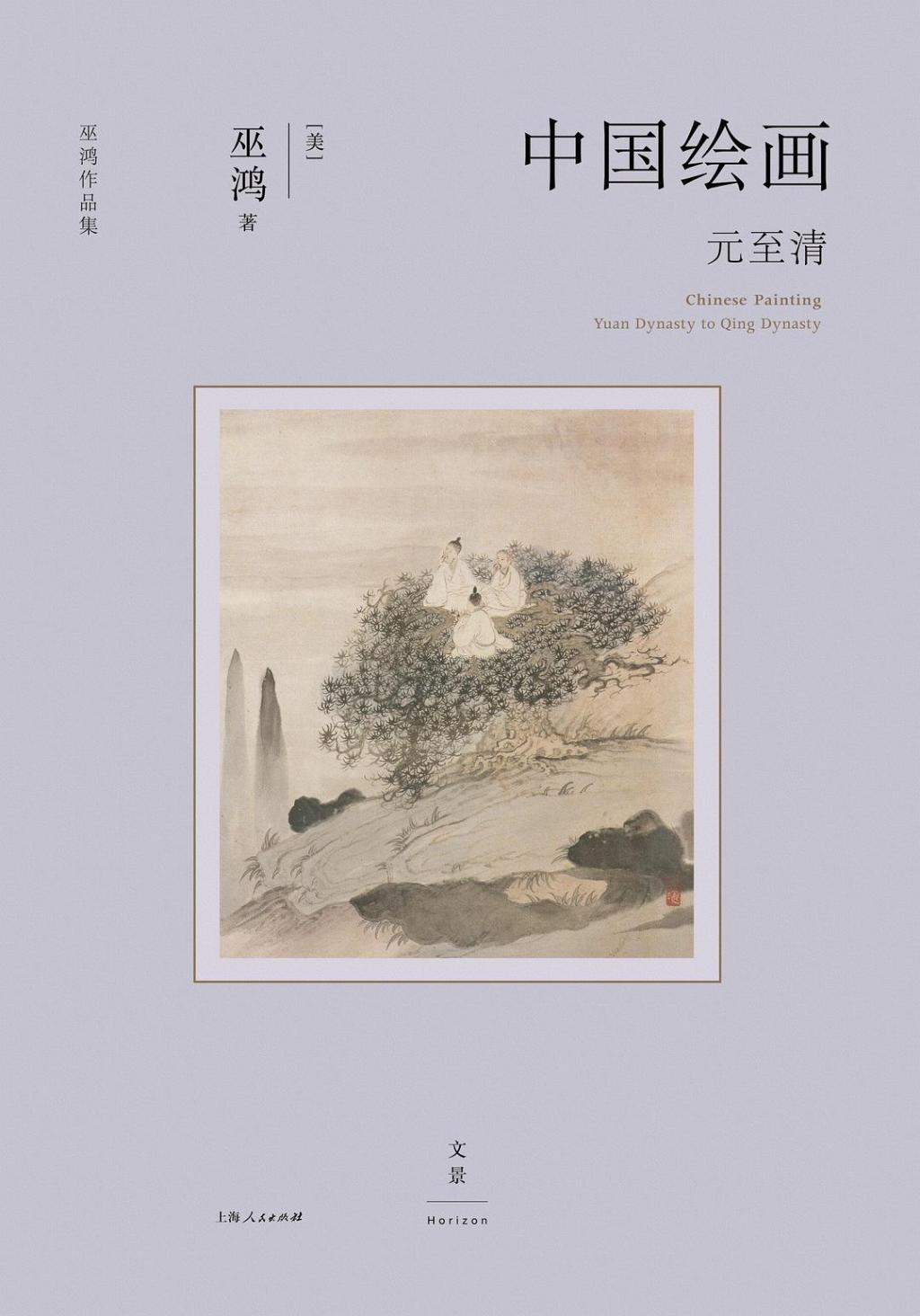
《中国绘画:元至清》,[美] 巫鸿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丨世纪文景,2025年3月版,600页,168.00元
巫鸿老师的《中国绘画:远古至唐》《中国绘画:五代至南宋》和《中国绘画:元至清》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于2022年、2023年和2025年出版,作为一个完整的绘画史系列,不仅为学界和读书界提供了一个既有学术深度和前沿探索性,同时也适合非专业人士阅读的中国绘画通史文本,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绘画史研究的方法论和叙事模式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在这里我想主要围绕以宏观历史研究意识重塑中国绘画史叙事这个重点来谈谈阅读《中国绘画:元至清》的一点体会。
在该书的“总论”中,巫鸿比较系统地阐释了研究方法、写作方式等问题:“我们需要在两个基础上确定各段中国绘画史的研究和叙述方法,一是绘画发展的阶段性,二是历史资料的留存状况。从叙述方法看,所采取的方式应该尽量全面地揭示绘画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不但关注形象和风格的特点,而且注意到媒材、内容、样式、画家、观者、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2页)这是在《中国绘画》前两卷就已采用的方法。另外,由于自元代以来的代表性画家的史料文献和可靠的传世画作数量大为增多,使美术史家能够以重要画家的个案研究发展为美术史写作的专门题材,因此出现我们熟悉的叙事模式:比较聚焦于单个画家,根据艺术成就和影响力给予不同的论述篇幅或从略。但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以这种独立画家为纲的叙事方法延续了传统画史的局限,“由于不把宏观历史潮流作为主要观察对象,难免会出现见木不见林之感。写作者对画家的选择也多因循传统看法,习惯性地将大量篇幅给予最著名的文人画家……非文人画家和女性画家或从简,或付之阙如”。在这里加了一个注释,说明这是一个鸟瞰式的宏观景象,并以例子说明“许多美术史家为改变这个状况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3页)。从这个细微处可以看到作者对于研究状况的清醒估计和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充分尊重。然后,“本卷希望尽力改变这种情况,给予后者更多的讨论篇幅;但更重要的是把单个画家纳入整体艺术潮流之中,在讲述更广阔历史运动的过程中呈现出画家个案”(3-4页)。这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应该把画家放置于宏观的历史进程和整体的艺术潮流中进行研究和论述,由此突破传统的绘画史研究与撰写方式的局限。听起来不太复杂,但是实际上这是迄今为止仍然有待真正解决的重要问题。
1983年我跟随陈少丰老师参与撰写王伯敏先生主编的《中国美术通史》(八卷本,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1988年)的时候,在鼓浪屿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上讨论的就是叙事模式、写作框架等问题,在这方面的共识还是遵守比较传统的规范,重点放在各门类美术史发展叙事的系统性与丰富性方面。在九十年代,学界思潮的涌动已经使人深感传统的美术史叙事模式亟需突破,但是如何突破却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方向,有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在通史性质的美术史叙事中如何处理美术史本身的发展脉络与整个历史文化发展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1996年我主持编写一部中国美术史教材(李公明主编《中国美术史纲》,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遇到的就是如何从传统美术史叙事模式中走出来的难题。这部教材面向的对象是美术学院美术史专业的本科学生,首先要确保的是所传授知识的正确性与系统性,然后是在研究方法、视野等方面开拓学生的眼界。因此我们这部《史纲》最后采用了比较折衷的办法,正文部分的叙事方式还是比较传统的,把相关历史文化研究的论述及研究状况放在各章的最后一节“余论”中,意在引导学生在掌握美术史的“内史”基本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比较宏观和前沿的历史文化议题。今天看起来这是一种类似“修正主义”的叙事模式,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模式与方法问题。
在九十年代末读到了由中美两国学者(杨新、班宗华、聂崇正、高居翰、郎绍君、巫鸿)合作撰写的《中国绘画三千年》(北京,外文出版社;纽黑文-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1997年),当时的确是很受启发,正如巫鸿老师(他在该书中负责撰写旧石器时代至唐代部分)后来在《中国绘画:远古至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的“自序”中所讲的,“《中国绘画三千年》的著述目的除了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之外,也希望改变中国绘画史的传统写作方式。”具体方法一是突破卷轴画的范围,在材料上把壁画、屏障、贴落和其他类型图画都包括进来;二是绘画发展的漫长与连续性,把从史前时代到二十世纪末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中国绘画:远古至唐》,1页)。或许应该说,面向国际学术交流也正是促进改变中国绘画史的传统写作方式的重要动因,这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学术在各领域产生不同程度的方法论变革的历史语境。方闻教授(Wan C.Fong)在《宋元绘画典范的解构:“形似再现”终极后中国绘画的再生》(Deconstructing Paradigms in Sung and Yuan Painting:Life after the Death of Mastering Representation)中提出,“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背景下研究中国画史,我们需要有一种有比较文化性的新模式”(王耀庭主编《开创典范:北宋的艺术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序言,台北故宫博物院,2008年,22页)。说的也正是改变传统的中国绘画史研究与写作模式的需要问题,至于何谓“有比较文化性的新模式”,可以有不同角度的理解和阐释。当年在方闻的这篇文章中,“典范解构”与“新模式”看来还是在从“状物形”到“表吾意”的模式转换,而今天要解决的却是巫鸿老师一直念兹在兹的历史性和整体性的叙事模式问题。
说到这里,我想进一步思考的是关于范式转换的问题。国内近现代史学界在经历过八九十年代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论争之后,更具有包容性和学术性眼光的研究范式成为许多学者的自觉追求。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新革命史”研究对以往传统革命史研究的偏差和“告别”革命史的偏差进行了双重纠偏,“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等的学科视角进一步拓展了近现代史研究的视野,激活了问题意识。从革命史到文化史、社会史、城市史等多学科对话与跨学科研究促进了对于新研究范式的探索(参阅黄克武《反思现代:近代中国历史书写的重构》,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从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范式”之争来看中国美术史研究,恐怕还需要从研究方法和叙事模式提升到更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范式”层面上来思考。又比如在清代历史研究中,“新清史”无疑提出了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范式,国内史学界对此争议较大,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未能深入展开。从宏观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来看中国绘画史研究,可以借鉴历史研究的“范式”之争来思考绘画史范式的重构问题。
为了从历史性与整体性的维度考虑绘画史的叙事模式,巫鸿在本卷中“尝试在朝代史框架中建立一个基本的分层叙事结构。以便对绘画的自身发展进行更为系统的考量”(4页)。也是延续《中国绘画:五代至南宋》的做法,这一分层叙事结构的最基础层面是媒材,即承载图像的不同的物质形式和不同的展示、观看方式,以及变化中的图像、题款、印章之间的关系,由此才能理解绘画在功能、意义及美学价值上的变化;因此在以卷轴画为主线的同时,另辟专门章节介绍重要的宗教、墓葬和宫室壁画实例。不过实际上在传统的编写方式中也有这种区分,重要的是在讨论“可移动绘画”的时候,需要继续注意手卷和立轴的使用场合、社会功能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如在“元代绘画”一章中要注意到文人对这两种形式的搭配使用。“适应着创作和流通的新需要,册页、折扇、条屏等绘画媒材也在明清时期得到普及。”(4页)
本卷叙事结构的第二个层面由文人画、宫廷绘画和商业绘画组成,其中此期最重大的现象是文人画成为绘画领域中活跃的、最有影响力的门类。因此在这个层面中特别关注和阐释了文人画的定义及相关问题,“由于文人画构成了元、明、清绘画中的一条主线,有必要在这里提供一个简要的定义。概而言之,本书将之看成是变化中的概念和实践,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发展、不断更新”(5页)。这个定义视角独特,不是条目式的定义,而是强调研究的方法与视角:打破固化的“文人画”标签与研究模式。下面这段论述非常有概括性:“值得注意的是,文人画在其长期发展中产生出多种风格,既有不同类型的水墨白描和写意,也包括青绿着色的复古格调。而某种风格一旦被贴上文人画的标签之后,也可能脱离表达文人思想感情的原初功能,成为宫廷中的陈设与装饰或者市场中的流通商品。我们因此不能简单地采用文人自身的视点。把‘文人画’看作一个完全独立的文化、艺术传统,而需要充分注意它在历史发展中的复杂性。从宏观层面上看,文人画在元代获得了最明确的独立的社会性和艺术性格;它在明、清两代的发展,则是通过内部的分化,以及与宫廷和职业绘画的交融和互动,逐渐融入了更广义上的中国绘画中。虽然对文人独立性的想象和强调从未消失,但随着文人阶层的逐渐衰落,文人画的内涵与性格也愈加模糊,最后只成为对特殊笔墨风格和‘诗、书、画’合一的代号。”(6-7页)应该说,对文人画的独立性的想象和强调虽然不会消失,但是更有诱惑力的想象是被贴上文人画标签的作品在与宫廷、市场的互动语境中如何产生功能与意义的解构与重构,尤其是想象“文人画”中的梅兰竹菊等标签式符号如何在想象中成为向权贵献媚或粉饰帝王人格的物事,会很有真实而荒诞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这里就有一个话语权问题,正如巫鸿所指出的,当文人画家更加频繁地担负起艺术批评家和理论家的责任的时候,“都来自文人画家对‘话语’的兴趣”(6页)。长期以来笼罩在“文人画”理论上的光环其实无非就是一种话语权现象。
最后,“本卷叙事结构中的第三个基本层次是地域,即画家的来源、工作地点和由此形成的绘画地理格局。利用学者们对文献数据的统计,以及对元、明、清重要画家生活轨迹的追寻,我们可以了解每个时期绘画教育和生产的地域、绘画中心与经济、文化、政治中心的关系,以及画家在宫廷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流动。进而对这些宏观运动中的个别案例加以分析,使我们得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了解绘画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变动关系”(7页)。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但还是要细心考量在“地域”概念中包含的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由于文艺史上的文学家、艺术家的群体现象相当突出,因此学界对于地域关系的研究一直有兴趣,问题是如何在考证与描述的基础上回应文学史、艺术史研究中的核心议题,提升整体性的研究格局。巫鸿在这里提出的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是地域研究这个层次的关键出口,在本卷开头关于元代绘画的生态格局的研究就是很好的说明。他以学界对于元代画家籍贯的研究为基础,指出元代绘画的地理格局显示为以大运河两端——元代首都大都(北京)和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苏南浙北地区——为轴心的二元状态,这一格局因此有别于以往朝代绘画中心在地域上的单点集中——不论是唐代的两京,还是两宋的汴梁和江浙。造成这个变化的原因是北京的政治地位自辽金以来不断提高和江浙地区经济地位的持续上升这两个趋势,于是人员的南北流动与元代绘画的关系成为要研究的重心问题(11-12页)。
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元代绘画的地理格局并非固定不变,其演进造成了不同时期内画家群体的不断重组以及地区性的社会活动。这就把我们引到本章叙事中的分期概念,即把元代绘画的历程划分为几个阶段,总结出不同阶段的特点和相互之间的关系。”(12页)从籍贯到绘画格局的地域性,然后深入到流动性、群体的形成与重组、与绘事相关的地区性社会活动的出现等议题,最后得出的是在时空关系中的绘画史阶段特征及相互关系这样的核心议题。这就是从地域层次切入的宏观与微观研究的历史性与整体性,也就是前面所讲的为了从历史性与整体性的维度考虑绘画史的叙事模式。
进一步来说,巫鸿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就是把籍贯、流动等地域层次的空间问题扩大到区域性的文化地理空间层面上来阐释,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可以在当代文化地理学谱系中找到相应的范畴。英国学者凯·安德森(Kay Anderson)等主编的《文化地理学手册》在地域与社会、政治、宗教、经济、文化、主体性、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关联议题中均把空间的分布作为重要特征来研究,提出了五个核心议题:作为事物分布的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作为含义的文化、作为行动的文化和作为权力的文化(凯·安德森等主编《文化地理学手册》,李蕾蕾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3页)。这五个核心议题怎么看都完全可以与绘画史研究的方法论与叙事模式结合起来,使绘画史研究与生活方式、精神体系和权力控制等研究维度紧密相连,这就是绘画史的历史性与整体性的重要方面。其实,巫鸿老师在他的《空间的敦煌:走近莫高窟》(三联书店,2022年1月)已经作出了重要的探索,一方面以“空间”角度和问题意识带动对原有敦煌材料的重新发掘和思考,另一方面是在美术史研究的方法论层面上提出带有普遍性意义的观点——虽然该书最后提出的“一个美术史方法论提案”被称之为“石窟空间分析”,但是从绘画史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它的方法论意义超出了石窟研究的范畴。
历史学家马勇的新著书名是《历史的原稿:晚清旧事的全新观察》(文化发展出版社,2025年8月),作者意在历史档案资料中重新观察晚清的历史。“历史的原稿”这个提法比较有意思,形象地表达了在历史中行动的人与后人的历史书写的关系:“原稿”存在于真实的历史语境之中。读巫鸿的《中国绘画》,可以看到他力图从宏观历史研究意识、媒材的物质文化视角、地缘文化政治、画家的社会分层与交往网络以及前现代社会的性别文化等多元维度追寻中国绘画史的“历史的原稿”。这部“原稿”曾经由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些地域的画家、文人、工匠、官员、士绅、青楼女子等各色人等共同谱写,但是远离了那个时代语境的后人会在各自的生活情境和研究语境的变化、制约中不同程度地在绘画史的“原稿”上涂写、修改、删削,就像一幅传统绘画在历经藏家、鉴赏家、评论者、撰史者层层积累的涂写之后,再经过现代学科中绘画史研究的分期、分类、分宗别流、经典化、标签化等学术生产程序的书写,在不同程度上已经从原来的历史语境中被剥离出来,被重新建构的历史叙事文本与“原稿”往往相差甚远。因此,研究者的职责就是尽可能从宏观与微观的层面上还原绘画史的真实“原稿”。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追寻与还原绘画史“原稿”的努力并不能完全依托于考古发现、文献出土等物质性史料的“补缺”发现,研究者的敏锐观察、问题意识和精准的判断同样也是揭示“原稿”的重要条件。例如,在论述钱选的花鸟翎毛作品在宋代花鸟画的构图基础上进行了文人化的提升,使其作品“务脱铅华,归之冲淡”这个问题的时候,巫鸿以1971年在山东邹城九龙山明代鲁王墓中发现的《白莲图卷》作为这种倾向的代表。他认为:“虽然由于在水中浸泡使其失去了原画的色彩,但残留部分恰恰显示出钱选对李公麟白描风格的长足吸收,以严整工细的线条描绘白莲出淤泥而不染的形象,左方的题诗进而点出此画的主题:‘袅袅瑶池白玉花,往来青鸟静无哗。幽人不饮闲携杖,但忆清香伴月华。’”(43页)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从作品上的残留部分揭示“原稿”面貌——原作风格、画家意图以及审美效果等——的成果。
我想起彼得·伯克(Peter Burke)对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的一段分析,他认为金茨堡把微观史学方法发挥到极致,同时指出微观史家的目标往往更具智识上的雄心,他们会像福尔摩斯那样从“对于琐屑细节的观察”中得出重要的结论。即使这些史家并不妄求从一沙一尘中揭示整个世界,他们也的确宣称要从地方素材中概括出整体性的结论(参见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63-65页)。只要读过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1976;鲁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和《线索与痕迹:真的、假的、虚构的》(Il Filo e Le Tracce:Vero falso finto,2006;鲁伊译,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3 月),都会明白何谓把微观史学方法发挥到极致以及“智识上的雄心”。可以说,作为美术史家的巫鸿有着同样的学术抱负——以细心、扎实的作品分析追踪所有有价值的线索和痕迹,以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和美术史家的图像分析、精湛技巧消解肤浅和固化的绘画史叙事。而且,伯克所讲的从地方素材中概括出整体性的结论作为一种方法,也正是巫鸿在研究中反复强调的微观与宏观结合、既要“见木”更要“见林”的研究方法。
在我看来,以“见木”与“见林”的关系来说,不仅是指单个画家与同一类画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是指向绘画史与宏观历史的关系问题。还是以“元代绘画”开头讨论的一个议题为例。元代建立不久后即开始实行的“四等人制”,虽然史学界对于是否有这个明文规定有不同意见,但是一种压迫性的民族等级制度无疑是存在的。巫鸿就此提出的问题是:与这种在行政系统中着意压制汉族的意图不同,中华文化中的诗词和戏曲、绘画和书法、道教艺术和工艺美术等多种重要传统都在元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甚至出现了前所未见的高峰,特别是对中国艺术发生了深远影响的文人画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波澜壮阔的艺术运动,一些蒙古人和色目人也加入进来,把“文人”的认同扩大到汉民族之外。那么,“这种看似对立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此时期内的文人画潮流有何特殊内涵?与元代社会条件的关系如何?其他绘画类型有何发展和变化?”(10页)这些显然就是在绘画之“木”与历史之“林”之间所提出的问题意识。应该说,在巫鸿的美术史研究体系中,宏观的历史研究意识是他重塑美术史以及更具体而言的绘画史叙事模式的重要学术路径。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暴露出时下某些仅仅醉心于在图像文本之间精耕细作的研究所存在的关键问题。
在重视宏观历史研究的同时,巫鸿当然没有轻视微观现象和图像文本细读的研究。在这里也有不同层次的区分。比如在论述了通过合理的分期把众多的元代画家——包括一些非汉族画家——组织进宏观历史叙事之后,他马上指出:“这一宏观叙事为讨论若干具有代表性的画家做了铺垫——这是本章概念结构中的最后一个层次。通过追溯这些画家的生活经历和艺术发展建构起一系列微观历史,一方面细化他们与一般性历史发展和文化环境的关系,另一方面突出他们各自有别的性格志趣和艺术建树。与其将这些名家的性格和风格固定化。此处的讨论尽量利用文字和图像材料显示他们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发展,并通过对代表性作品的细致分析将这种历史性显示出来。名家和名画因此不是孤立的,而是被置于变化的元代政治、社会和文化原境之内,通过对它们的细读,将宏观的历史叙事具体化、个性化。”(15页)这里谈到的几个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把宏观历史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重塑绘画史叙事的实际操作问题。在重返的历史语境中通过对画家和作品的细读,“将宏观的历史叙事具体化、个性化”,这就讲得很清楚了。
法国艺术史家达尼埃尔·阿拉斯(Daniel Arasse)曾经指出:“通过细节把握绘画这一研究方式可令通常情况下不为人所见的东西显露出来。……这些思考同时也表明。细节对于艺术史家而言是多么重要的‘体验’场所,它的次要性只是表面现象。细节性关系一旦进入艺术史家的视野,便会令艺术史的一系列经典问题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尼埃尔·阿拉斯《细节:一部离作品更近的绘画史》,马跃溪译,三联书店,2023年9月,3页)阿拉斯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画面上的细节在被观者发现、注视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靠近画面观看的人获得了何种“惊奇感”或“回报”?以及如何在细节中发现画家在其作品中“现身”的隐秘成分(同上,5-6页),目的是“发掘细节在历史中——在画作酝酿过程中也在观者观看过程中——得以发挥的独特功能”(同上 10页)。这几乎也是对巫鸿的绘画史研究的一种描述和评价。
书中有一个例子颇能说明巫鸿在图像分析中的体验、惊奇感和细节发掘如何使一幅人们熟悉的名作“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在分析王蒙五十九岁(1366年)时画的《青卞隐居图》的时候,他说在讨论其笔墨表现之前,首先应该注意它的立轴媒材和相应构图。“一个极为关键但很少被注意的特点”是这张画远较一般的元代挂轴狭窄,只有意识到这一媒材的特性才能历经此画极不寻常的构图方式:峰峦层层堆积、扭曲盘旋、向上攀升,“整个画面被一股自下而上的气势驱动,如同爆发的火山正从地涌起”(125页)。“所有的传统山水画元素都失去了固有的稳定性,都在反叛着既有的秩序。”(126页)“画家肯定是有意地设计和创造出了这种诡异的不稳定感和情绪的爆发:如果把目光移近,我们就会发现王蒙的焦墨皴擦往往超越了物象的边界(图1.63d)。与其说是描绘具体的山水人物,不如说这些快速的墨迹表现的是画家不可约束的感情,被融入他所创造的这个充满共情的山水世界”(同上)。说实话,这幅名作我也比较熟悉,肯定也要选入我们的《中国美术史纲》,但是巫鸿这种在画面上体验到的情绪、创作意图和在细节发现的“不可约束的感情”是在我们的叙事中所没有的。
在宏观的历史研究意识中,时代政治与艺术的关系自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在这个问题上巫鸿对于时间尺度中的政治与艺术有相当敏锐的感受和分析。在前述《空间的敦煌:走近莫高窟》一书中,巫鸿提出了关于莫高窟的“外部时间”与“内部时间”的讨论,而所谓的“外部时间”(extrinsic time)具体来说就是以中央政权更迭为依据的“朝代时间”(dynastic time),严格说是一种“国家政治时间”,其叙事模式是以此构成一个囊括其他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线性结构(《空间的敦煌》,75页)。在本卷的“明代绘画”开头部分的第一节标题就是“洪武断层”(142页),一个严酷的“国家政治时间”横亘在绘画史发展的“内部时间”之中。在概要地论述了朱元璋对南方士人的种种迫害案例之后,他指出:“历史学家认为这一系列镇压行动反映了朱元璋对文人态度的变化。”(152页)新朝初建之时,为了重建行政机构而通过留用和举荐等途径选拔官吏,并下诏招揽天下士人以任用之。“但当了皇帝之后,他对文人的使用成为强迫性的,认为士人若不能唯命是从便没有存在的必要,在格杀勿论之列”(同上)。因此,“文人画这门艺术在如此高压的政治气氛中遭到了巨大打击,许多著名画家命丧黄泉,元代江南士人建立的社会网络基本被摧毁。苏州这样的文人绘画中心不复以往的光芒,直到百年之后才重新恢复其文化重镇的地位。在朝廷里服务的宫廷画家往往别无选择,只能揣摩上意,以作品点缀升平。从各种记载看,洪武时期供奉内廷的画家地位很低,受到的惩罚则极为严厉,处死之事屡有发生。……在如此严酷的统治下,画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难以发展新的题材和画风。虽然这种状态在明太祖之后有所改善,但仍给明代的宫廷绘画定下了基调。”(153页)
接下来,虽然明代宫廷绘画有过鼎盛时期,以多姿多彩的风格和样式特点形成了明代院体画的特色,“但这并不意味着画家享有更多的创作自由”(174页)。具体来说有几个方面的现象。一是不少记载揭示宣宗对宫廷画家十分严厉,画家动辄被处罚、被削官贬谪,因此人人自危,“这导致明代宫廷绘画在内容和趣味上趋于狭窄和表面化,难以产生真正打动人的作品”(同上)。这是高压政治之下的艺术创作必然呈现的颓势。二是“一旦入宫,宫廷画家的创作范围就主要局限于紫禁城中,无法参与绘画的广阔社会实践,更不可能带动北方画家的整体崛起。宫廷绘画在题材和风格上的多元性及其对皇帝绝对权威的屈从,也使它难以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发展逻辑的画派”(174-175页)。不过话是这么说,争取进宫恐怕还是太多画家的自我选择,这也不难理解;三是宫廷画家被编制于御用监及锦衣卫体系之中,与文人的关系也愈益疏远。到皇帝不再热心绘事之时,大量的捐官现象使宫廷画家的社会地位更为低下,加上锦衣卫机构的声名狼藉,这诸多因素都使宫廷绘画在明代中期和晚期日趋衰微(176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学家的通史叙事笔下,对于从朱元璋到朱棣如何滥杀功臣和推行特务政治自然是论述的重点(如樊树志《国史概要》,第四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292-301页);在绘画通史中也会谈到自朱元璋当皇帝以后“在短期内这么多画家被处死,在中国画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中国绘画三千年》,198页)。但是像巫鸿在“明代绘画”中这样把宏观历史与绘画史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论述,把“国家政治时间”与绘画史“内部时间”的关系作出如此深刻和精准的分析,这是绘画史的“重塑”中很重要的一个维度。“洪武断层”这个标题的力度令人心惊,仿佛是来自古代的“时间开始了”。
无论是在宏观的、整体性的历史研究还是在绘画史的微观研究中,能否重返历史语境并从中能够洞察历史的真相,与研究者的个人语境有极为紧密的联系。如教育背景、经历、价值立场、思想观念和情感体验等因素,否则的话重返就是一个问题:如何选择重返的目标?能否在重返中观察和体验到有真正价值的东西?巫鸿老师的宏观历史研究意识与重塑绘画史叙事的努力及成果给我们提供了具有典范意义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