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涛评《线索与痕迹》丨就虚而近实

《线索与痕迹:真的、假的、虚构的》,[意]卡洛·金茨堡著,鲁伊译,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3月出版,478页,118.00元
即使是专业的历史学者,如果没有读过卡洛·金茨堡的既往作品,特别是《奶酪与蛆虫》《夜间的战斗》这两部,直接上手他的新文集《线索与痕迹》也是颇为头痛的。你很难想象一位年事已高的学究在他庞杂散漫的知识网络里采取精力旺盛的蛙跳战术,反复迂回后才对议题发起冲击。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阅读这本书的体验大概类似于观看自己并不熟悉的体育节目,你无法判断一位攀岩高手会选择哪一块石头来借力,可能会充满好奇地看下去,也可能会索然无味地关掉电视。
因此要为这本书写一篇提纲挈领的评论也是困难的,难在不知从何说起。以该书第八章“寻访伊斯拉埃尔·贝尔图乔”为例,开头几段关于霍布斯鲍姆的分析会让你以为他要说明历史研究的转型,他却戛然而止,通过文学作品《红与黑》的于连之口引出一个叫做贝尔图乔的历史人物,将这个名字留给读者后又开始阐述真正的主角马里诺·法列罗(Marino Faliero)有几种版本,其中拜伦的版本又有怎样的影射,他如何选择和运用史料。接下来作者开始考证贝尔图乔的名字和身份,继续寻访虚构和历史真实之间的分歧,最后得出结论:在连续的语境变化中,人物身份和事件情节不得不加以勘误,垂诸后世的历史形象也随之消散分解了。(237页)此处终于点题了霍布斯鲍姆的忧虑:相信历史研究能够通过证据和普遍接受的逻辑规则来区分事实和想象、有可能的和无法验证的、实际发生的和我们想要让其发生的,这样一种信念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
听起来似乎有点虚无,但这艘“忒修斯之船”的确是历史学者们普遍遇到的困境——如果把一桩历史事件比作一艘船,时间、地点、人物等诸因素都是船的部件,当我们换掉那些有问题的部件后,这艘船还是原来那一条吗?专注于微观史学的金茨堡对此感受更深,因为他频繁地见识到细节的败坏会导致多元化的分析结果,使得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之间泾渭不分。但大师毕竟是大师,他并未因此陷入各种怀疑论立场中,而是提出一个充满建设性的问题:任何叙事——无论真的,假的,还是虚构的,都暗含着某种与真实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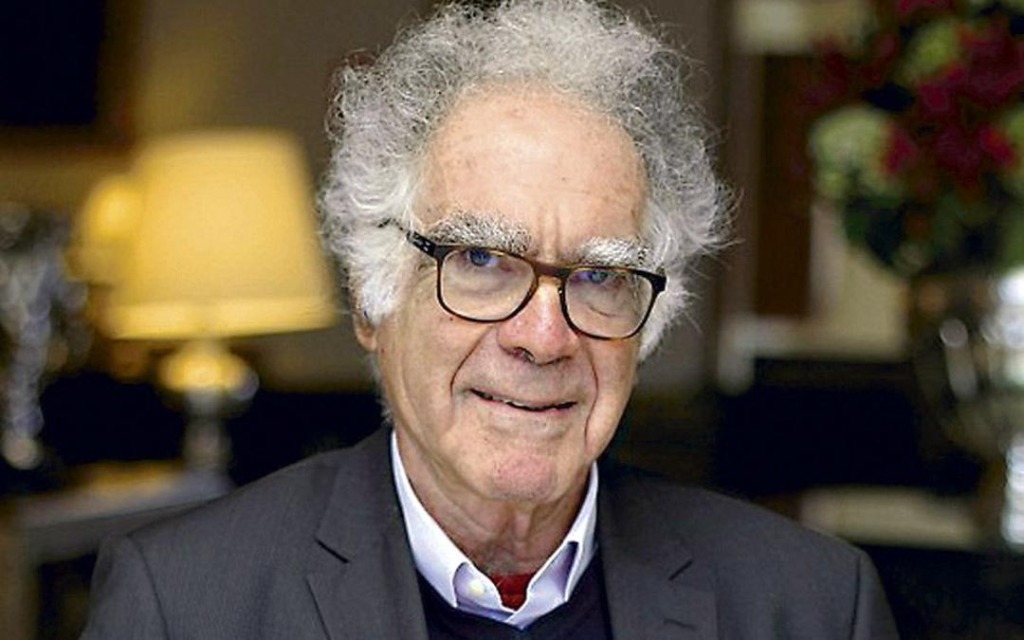
卡洛·金茨堡
一、本有之事和历史叙事
为了在金茨堡光怪陆离的思想世界里找出一根合适的线头,让我们从本书第十一章“孤证:对犹太人的灭绝与真实性原则”开始说起。“孤证不立”,这条逻辑观念犹如钢印一般镌刻在每一位历史人的脑海中,它的正确性毋庸置疑,但金茨堡偏偏不信这个邪。他首先通过辨析犹塔帕塔事件和梅察达之围说明,孤证不为证(testis unus,testis nullus)来源于罗马法和犹太法法律传统中共同拥有的一项准则,即拒绝承认审判中单一证供的合法性。接下来作者敏锐地指出,尽管这一准则在史学上的推广无可争议,但若严格按此标准处理重要的历史文献,许多真实事件将因为“孤证”而消散;反之,以貌似严谨的实证主义态度来处理历史事件也会带来糟糕的后果,如福里松等学者的大屠杀否定论在道德和政治上都令人反感,却难以在僵硬的实证逻辑体系中将之驳倒。
这里所谓的真实事件,就是克罗齐的“本有之事”(cosa in sé),在历史上确凿发生过,而我们并不知道。相关的一份文献只是一个事实,行事者为一种事实,叙事者为一种事实,每一份证词其实都是对自身的见证——见证自身时刻,见证自身起源,见证自身意图,除此无他。所以任何文献无论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直接材料,或曰一手材料,仍然与真实(“本有之事”)保持着疑问重重的关系。
以妇孺皆知的中国历史来举一个例子,首先让我们预设一件“本有之事”:秦二世三年八月的一次朝会上,赵高通过与群臣的交流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但是他使用了何种手段和方式,我们并不清楚。目前最权威的文献《史记·秦始皇本纪》作了如下的历史叙事(storiografia):
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
这个指鹿为马的故事被后世当作了史实,但后人并不太容易接受这一情境的合理性,且不说一头野生动物在公卿满座的朝堂上如何保持安静不吵不闹,单是想象群臣为此争论的样子就十分荒谬。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便认为,这个故事是非常优秀的喜剧,但很难直接当成史实,司马迁所以描写得如此生动,是因为他参考了一些文字资料,比如汉代流行的偶语剧。优旃两人一组,时而跳舞时而进行议论来表现著名的历史事件,这种剧常常在宫廷和民众聚集的市场上表演,因此传播范围较广,其脚本很有可能进入到司马迁的选材之中。
某个历史叙事很像虚构叙事,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金茨堡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我们会把一本历史著作中讲述的事件当成是真的,毕竟一个假的陈述、一个真实的陈述和一个虚构出来的陈述,从表现形式上看并无任何不同。于是他剖析了历史叙事的两种套路,去寻找那些保证真实性的要素。
二、生动描述与粗鲁不文
“生动描述”(enargeia)这个术语专指演说家提供全面的信息来打动和说服公众,以传播他所陈述的真相,金茨堡用以形容荷马作品的风格——生动是描述的目的,真实就是生动带来的效果。如《伊利亚特》里描写战斗场面的一段:
地面上,迅捷的阿喀琉斯继续追赶赫克托耳,毫不松懈,像一条猎狗在山里追捕一只跳离窝巢的小鹿,紧追不舍,穿越山脊和峡谷。尽管小鹿藏身在树丛之下,蜷缩着身姿,猎狗冲过来嗅出它的踪迹,继而奋起追击——就这样,赫克托耳怎么也摆脱不了裴琉斯足力雄健的儿子。
且不谈神话人物和故事的虚构性,荷马的书写显然是一种直接目击(autopsian)和身临其境(parousian),将一场追逐戏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历史学者在面对这种文本时也会恍然觉得,荷马当时就在普里阿摩斯的城垣上目睹这一切,但理性很快便作出否认,进而产生一种意识:我们对往昔的认知只有一些残缺的片段,当这些断断续续的历史被串联成故事时,必然会被填充大量的想象。基于此,十六世纪的语文学家和古文物研究者罗博泰洛指出,历史的方法论要素与修辞学同属一类,修辞乃是历史之母。
这种历史书写的方法引发的争议持续至今,例如当代汉学家史景迁的写作向来备受质疑。在其作品《王氏之死》中,他主用的史料《郯城县志》尚可算作信史,县官回忆录《福惠全书》则多有荒诞不经之处,纯文学作品《聊斋志异》的引用更是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议。史景迁对此解释道,“蒲松龄正是生活在本书所涉的时代,尽管是小说,它代表了一种见解……我的任务就是当一个事实捕捉者,去寻找那些确实的拼图”。在这些“不靠谱”的史料支撑下,史景迁对于十七世纪清代中国一个边缘县城的普通妇人的描写达到了巨细靡遗的程度,写她穿一双红布软底的旧睡鞋,内衫是蓝的,薄薄的内裤是白的;写她被丈夫掐死时,她的腿使劲抽动着揉碎了席子,踩穿了席下的草垫子。这是虚构的,因为史景迁不在现场;这又是真实的,这一番“生动描述”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社会像王氏这样的普通妇人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和悲惨命运。
在《线索与痕迹》第三章中,金茨堡总结了另一种相反的历史书写手法,并借用语法学家格利乌斯的说法将其命名为“粗鲁不文”(subrustice),是一种不事雕饰的、旨在打破古典结构的随意文风。金茨堡从蒙田的《论食人部落》出发,指出其刻意为之的写作风格和十六世纪三十年代粗犷自然的流行品味密切相关,并进一步分析了蒙田对于文明和野蛮的反思——“这些人被我们视为野蛮,恰在于其未被人之机心所范,依然近于素朴本原。”认识到距离和多样性的蒙田努力去理解对方的风俗并转换了视角,从而发现了另一种书写历史的可能。用贡布里希的话说,品味是一道滤镜,不但会带来道德和认知上的后果,也会产生审美上的影响。金茨堡想说的是,以文明自居,以当代社会的思想观念先入为主,必然会以自负的偏见来审视历史。
三、反照技法和间离效应
在第六章分析奥尔巴赫对伏尔泰的解读时,金茨堡提醒读者注意两个艺术上的手法,伏尔泰的反照技法(Scheinwerfertechnik)和布莱希特的间离效应(Verfremdung-Effekt),两者在造成“陌生化”的效果上极其类似。“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由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就是通过改变习惯化的感知和描述手段来使审美主体获取新的认知,例如将一个日常物件变成某种圣物,或反其道而行,将某个神圣事件描述得稀松平常。再比如士兵在战场上击鼓迎敌,作家们通常会把这个场景写得慷慨激昂,而在伏尔泰的笔下,那不过是“身穿红衣,头戴二尺高帽的嗜杀狂徒”“拿着两根小棍子,击打着紧绷的驴皮发出噪声”。
一位纯粹的历史学者是不会在意这些文学问题的,而作为通才的金茨堡敏锐地发现,对伏尔泰作品中间离手法的功能进行近距离观察,便会看到一个更复杂的故事出现。这位启蒙主义的大师在他的作品中大量使用间离手法来嘲笑不同的宗教和信仰,以及当时的法国社会,反照出的是他对思想和贸易自由的赞许。不过这种超脱性的视角也无法使伏尔泰对种族问题的看法超脱于时代限制,想象一位来自太空的旅行者将人类看作一种动物:“有人高出黑人一等,正如黑人优于猴子,猴子优于牡蛎”(165页)。对伏尔泰来说,人类历史是在等级制度的框架内发展出来的,奴隶贸易也是一种合理的商业贸易,其中的残酷与不公只是人的观念而已。借着埃里希·奥芬巴赫对伏尔泰的细读,金茨堡神奇地找到了启蒙主义和纳粹主义的交汇点——“不宽容和宽容以相反的方式促成了同一个后果”。
在第九章对司汤达的讨论中,金茨堡再次提及了奥芬巴赫和他的著作《摹仿论》,并提醒读者这本书的副标题叫作“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奥芬巴赫的主要理念就是历史的发展通常会生成多种抵达真实的路径。所谓“现实的再现”,不就是历史学者们孜孜以求的“重建历史现场”吗?不同的是,史家常常摈弃短期、偶发、特殊的信息去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在奥芬巴赫看来,透过一个意外事件、一个普通人生、一个随意撷取的片段,我们可以达成对总体全貌的更深入了解。(243页)换句话说,借助一些基于虚构的人物和故事,也有机会抵达更深层次的历史真相。有这种观念的人在正经的历史界恐怕为数寥寥,但在文学界却多有知己。比如对卡尔维诺来说,哪怕童话故事也是真实的(le fiabe sono vere),故事真实的原因是它们平实地反复重申人类的真相——美与丑的命运,恐惧与希望,偶然和灾难。
也许有人认为,文学求美而历史求真,历史学者绝对不应采信不够坚实的史料去构造历史,但平心而论,难道我们今日的历史研究不也充斥着“间离”的手法吗?特别是在近现代史研究中,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和几成定论的历史事件,学者们几乎不可能作出颠覆性的研究成果,只能在细节上转换视角或使用“感情史”“观念史”等新手法使熟成的历史“陌生化”,酿成滋味相仿的旧瓶新酒。十万八千里的跟头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这种日渐流水化的作业方式看似一次再创造,实则受到既往文本和个体趣味的双重影响,也就是奥芬巴赫所反对的“被现代意识所感知的历史真实”。
四、无知惑见与了然知见
历史学者曾经有一种信念,相信借助证据和普遍接受的逻辑规则,历史研究能够区分事实与想象,区分有可能的与无法被验证的,区分实际发生的与我们想要让其发生的。(218页)如今这种信念已然动摇,史学无论如何都无法重构完整的过去,于是又回到第一章提出的核心问题:借助修辞技艺(包括虚构)而再现的往昔是否值得信任?金茨堡在本书第七章以巴泰勒米的作品探讨了这种可能性。巴泰勒米虚构了一位叫做阿纳卡西斯的青年前往希腊旅行,他参加了许多宴会,会晤了一系列名人,并对当地人的风俗习惯进行了观察,这是一部游记,但不是一部历史,因为其中充满了“历史学家不允许援引的微末细节”:
她的梳妆台首先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看到了银盆和银壶、不同材质的镜子、固定发髻的发针、烫头发的烙铁、宽窄不一的束发带、拢起头发的发网、黄色的染发粉、各式各样的镯子和耳环、成盒的唇膏和铅粉以及染睫毛的烟黛,还有保持牙齿洁净的一应物事。
这种不知所谓的罗列在历史学家眼里是琐屑而无意义的,阿纳卡西斯作为笔下人物目光短浅,所以他提供的信息是一种缺乏利用价值的“无知惑见”(sguardo interrogativo);但在其背后却是熟稔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历史的古文物研究者巴泰勒米,他的智识保证了《青年阿纳卡西斯希腊游记》中关于宗教仪式、节日庆典和生活习俗的部分称得上“了然知见”(sguardo consapevole)。因此这本书尽管不能算是一篇系统的古文物研究论文,也不算一个历史叙事,但仍然能提供相当的真实性。类同于《风俗论》《雅典人信札》等非典型历史叙事,这种书写的价值在于“它们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希腊人和波斯人的言行举止,让我们得以借此更充分地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远胜于那些严肃的古文物研究者长篇大论的高头讲章”(211页)。
真实与虚构的混合杂糅一直在挑战现有历史书写的界限,金茨堡所举的案例是用虚构去拼凑真实,更常见的做法是将真实元素编织在虚构作品之中,英国作家拜厄特在《论历史与故事》以约翰·福尔斯的小说《幼虫》详细说明了这种趣味。这部作品的历史背景是英王乔治二世在位期间,其中逐月重现了1736年的《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以设置“历史编年”的感觉,也运用了许多真实的事件,包括消逝已久的接骨师、猎场看守、绞刑和拦路抢匪等历史片段,但作者也无意创造一部历史小说,而是希望通过对这个“遥远的18世纪过往的感觉和口吻”进行再创造。这部文学作品产生的效果便与《奶酪与蛆虫》类似——让现代的人们真切看到那些无名的、已逝的人物在他们已经荒芜的世界踟蹰穿行的景象。他们的故事是历史的一部分吗?越来越多的人对此持肯定态度,即使这些人物无足轻重,他们也来自于菲尔丁所谓“鸿篇巨制、真实无虚的自然之书”。
到了二十世纪,作家们愈发不满足于将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囿于大事件和权力者,而是用修辞和智识尽可能还原历史的面貌和声音,追求“不可能的精确性”(《论历史与故事》121页)。史学界也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也开始唱起对布罗代尔及年鉴学派的反调,法国新史学、历史人类学以及金茨堡的微观史研究都采取了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的态度。金茨堡的态度是相当温和的,他并不以微观的可靠性来否定宏大叙事,提出既要关注那些业已确立其重要性、甚至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主题,也要关注此前被忽略的、或者被贬为低级浅薄的研究领域,如地方史主题等。(395页)我们也可以将金茨堡的微观史思想理解为“无知惑见”与“了然知见”的互通——当我们放大观察的尺度时,并不能看到一个连续性的场景,而仅仅是历史画面的一帧;而将这些蛛丝马迹的线索用假设、怀疑与不确定的动机串联起来,会发现“本有之事”并不等于史料文献,而是存在于同之前和之后的系列事件的关系之中。
总体来说,金茨堡提倡的微观史学和“线索式研究”(indizio),反对的是长久以来对于档案史料的过度依赖和由此形成的一些固有观念:史料越权威越好,越完整越好,越多样越好。他用诸多扎实的个案分析展示了一种危险,由于历史书写的扭曲和话语权力的污染,试图解释一切的宏观史学遮蔽了历史的真实风貌。而那些细微的、零碎的、向来不被重视的材料,无论真的、假的还是虚构的,都为我们提供了重建史实的可能。他提醒我们,史料的价值不在于共性,而在于其独一无二的“特异性”,对那些琐碎细节的摸索有助于我们触及历史的毛细血管,感受粗糙而有温度的文化褶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