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玮琳评《以竹为生》|重新认识现代中国工业化中“看不见的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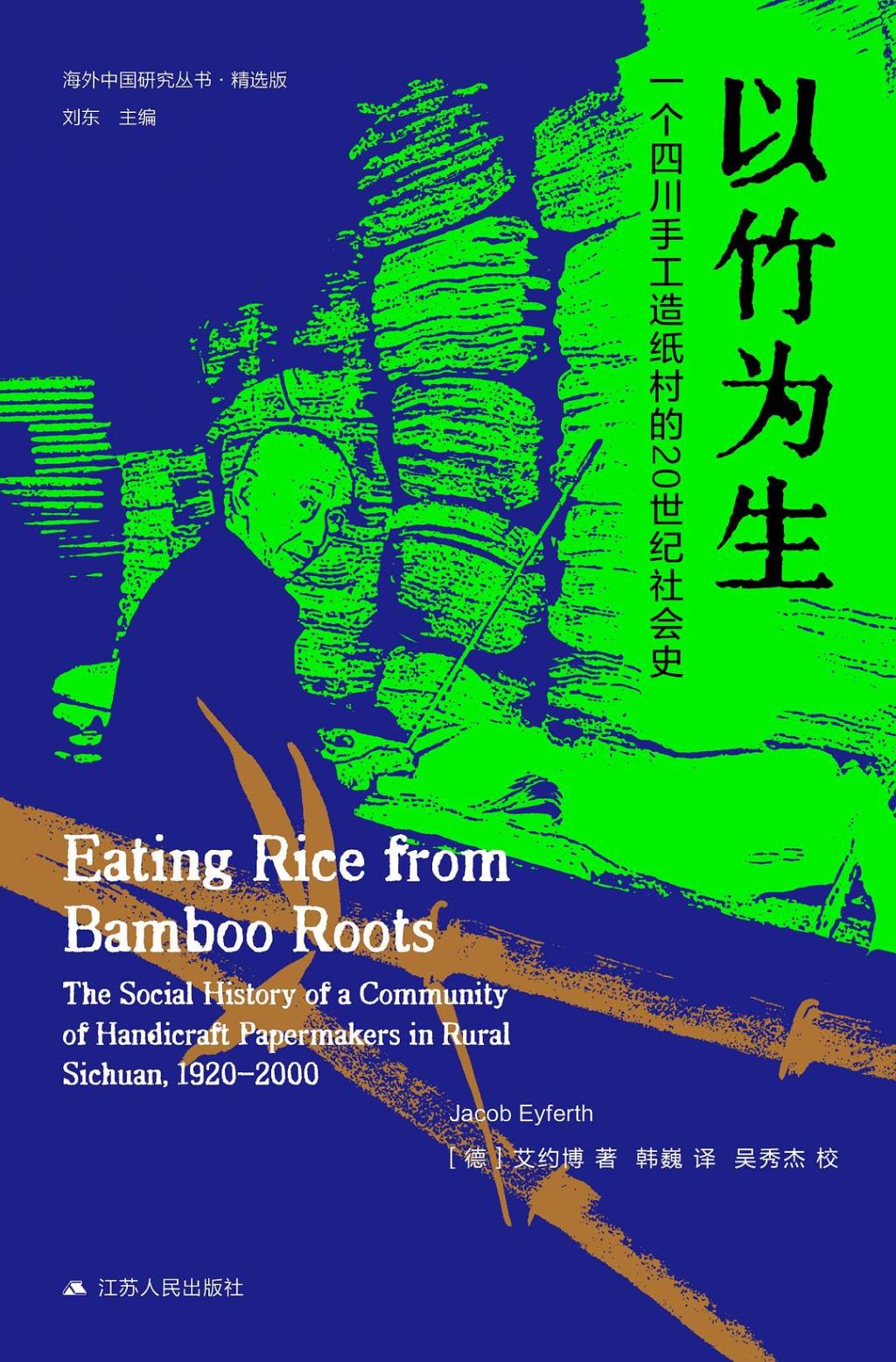
《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德] 艾约博著,韩巍译,吴秀杰校,江苏人民出版2024年5月出版,340页,98.00元
2009年,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了艾约博(Jacob Eyferth)的Eating Rice from Bamboo Roots: The Social History of a Community of Handicraft Papermakers in Rural Sichuan, 1920–2000。该书对四川夹江县石堰村手工造纸业的细致描绘,在国际中国学界引起广泛关注。2016年,经韩巍、吴秀杰译校,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推出了中文版《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2024年又将其收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精选版”。这本书的再版,恰好响应了学界对技术史、手工业史与社会史的关注再起。
艾约博于2000年在莱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先后在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罗格斯大学历史分析中心从事研究,目前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历史学与东亚语言文明系。他长期致力于探讨中国社会史中非精英群体的劳作经验与技术实践,发表过若干关于中国农村集体化、农村手工业技术与劳作的论文。《以竹为生》一书在其博士论文“吃竹根饭:一个华西造纸社区的历史,1839-1998”基础上修订而成,通过一个手工造纸村的个案,对劳动过程、技能传承、性别分工与社会嵌入等问题进行长时段考察,一举奠定了作者在劳工史与农村社会史领域的专业地位。
自该书中英文版问世以来,学界已有近十篇书评,高度评价其对县志、地方档案、行业调查、民族志与口述史资料的结合运用,认为它生动再现了二十世纪四川乡村手工业的日常状况;同时也肯定了该书的理论探讨价值。艾约博针对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兴衰这一经典命题,通过“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与“去技能化”(de-skilling)的分析维度,挑战了诸如农村工业化来自城市溢出效应、并且是现代化建设的自然路径的传统叙事,试图揭示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政策干预与区域经济变迁的复杂因果。尽管夹江手工造纸业是小规模、分散型家庭作坊,但是艾约博并不视之为“落后的残余”,而是解读为一种对生态与市场条件的适应性产业,蕴含高度的专业技能与市场价值。在“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的解释模型中,这类高度市场化、区域性专门化的家庭手工副业,本可成为通向现代经济的路径之一;然而在强调“现代工业化”的过程中,传统手工业技艺不再是社会中受尊重的资本,反而成为一种“低端劳动”,构成了现代化的悖论。

《以竹为生》的上述观点,源自作者对“结构性约束下的日常生活”的持续关注。近年来,艾约博曾发表过关于文浩(Felix Wemheuer)的《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社会史:1949-1976》(A Social History of Maoist China, 1949–1976,2019年)、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r)的《红绸:中国长三角丝织厂的阶级、性别与革命》(Red Silk:Class, Gender, and Revolution in China’s Yangzi Delta Silk Industry,2021年)、周淑萱的《从林场到锯木厂:劳动、性别与中国国家的叙事》(From Forest Farm to Sawmill: Stories of Labor, Gender, and the Chinese State,2024年)等海外中国学新作的书评。这些著作均关注并讨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产业变迁中的劳动再组织,尤其是性别如何在劳动控制与分配中被制度化的问题,呼应并延续了艾约博对国家工业化叙事的反思。
在《以竹为生》之后,艾约博投入了关于四川、陕西和华北农村家庭妇女纺织的民族志与历史学研究。从造纸业男性工匠的技能与劳动地位,转向女性的家庭手工劳作,他依然试图解释,这些被边缘化的劳作,如何在国家工业化话语下持续存在,并在地方社会中发挥关键作用。艾约博注意到,在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即便国家大力推动工厂化生产,农村妇女依旧长期从事费时费力的家庭纺织。除了特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制度性短缺,家庭纺织的“社区再生产”(community reproduction)功能亦至关重要。这种非正式的、甚至被贬低的家务性劳动,不仅是一种物质生产,更是农村日常礼仪循环(嫁娶、丧葬、馈赠)中必不可少的交换媒介。农村妇女的纺织、养猪、拾柴、采集等其他非工资性劳动,被国家隐形吸纳,并且成为农村社区运行的必要支撑——这正是国家经济发展背后“看不见的劳作”。
从“去技能化”到“看不见的劳作”,艾约博的研究逐步将技术史、劳作史与性别史交织在一起,转向社会再生产功能的探讨。社会再生产涵盖生育、抚育、教育、家务、食物与衣物制作、礼物交换与人情往来等活动,它既与生产相对,又是生产的前提。地方层面的社会再生产,不仅在家庭内部展开,还通过社区互助、宗族关系、礼仪循环与地方市场维系着自身的延续和稳定,这正是所谓的“社区再生产”。
在《以竹为生》中,尽管没有刻意强调这一概念,但作者对夹江山区的社区和宗族、市场和社区以及家庭生产的分析,实际上揭示了类似逻辑。他特别强调“技能的共同体”(详见该书第二章“夹江山区的社区和宗族”),指出造纸不仅是经济活动,更是一套嵌入社会关系的技能体系,既包括打浆、刷纸的技术性知识,也包括如何寻找买家、与邻居相处的社会性技能。这些技能更像是一种社会资本,通过亲属关系、婚姻、学徒制与村落网络,被管理与传递。夹江山区的经济活动完全是围绕这种社会资本展开的,因此,社区内部联结的核心逻辑超越了单纯的血脉继嗣。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艾约博进一步提出,二十世纪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技能、知识、技术掌控的再分配”,他甚至认为,在技术转型的层面,“中国的革命”是“技术掌控权大规模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一线生产者手中转移到管理层精英手中,从女性身上转移到男性身上”,而中国的“城乡分野部分地是由于城乡之间在知识分配上的变化所造成的”(导论,第2页)。
笔者的研究聚焦抗战时期西南地区造纸工业的技术创新与生产调整,因此,也将视野延伸到了成都与乐山之间的夹江山区。二十世纪战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全面战争,因此生产动员成为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纸张是战时重要的军事资源。在战时经济体制下,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增强了自给自足意识,采取战略物资的统制政策并寻求生产能力提升的技术创新。战时中国也概莫能外。抗战军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在西南地区形成新的政治、文化、工商的中心,也开始在《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的整体规划下,对西南地区传统手工纸的“山乡造纸”模式进行改造,将利用现代化学工艺改良中国竹纸的科学实验和战时自主工业体系建设的进程联系起来。这正是《以竹为生》里夹江造纸业命运发生急剧转折的开端。
艾约博对于战时来自沿海地区的技术专家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予以严厉批评,认为这些五花八门的改革提议,“从廉价可行的方案(从水泥浸池,使用更剧烈的化学剂)到天马行空的方案(撤销所有用竹浆制纸的工厂,代之以木浆制纸的工厂)……几乎全都认为手工业生产技术是低效和浪费的,这往往显示出他们对当地情况一无所知”。(121页)出于对专家“套取”槽户生产知识的批判性看法,他仅用五页篇幅描述了战时的竹纸改良。而笔者的研究,恰好关注的是艾约博并未过多着墨的这些技术专家。战时中国的造纸专业人士与实业家,亟力发展“新兴纸业”,改良土纸,希望找到一种既可突破生产原料限制,又可与分散型手工作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的应急办法。以中央工业试验所纤维研究所为代表的科学家设想将现代造纸的化工原理或生产工艺,经过最大程度的精简,应用到西南地区特有的植物纤维材料上,并通过系统地组织、帮扶和管理生产厂家或槽户,实现在完全人力或半机械设备的有限生产条件下最大限度的生产动员。他们在战前和战时所进行的大量民族志调查、实验室研究和试验工厂建设的种种努力,及其对战后中国造纸业发展方向的影响,构成了《以竹为生》叙事的另一侧面。
《以竹为生》不仅让我们重新理解了传统手工技艺在现代化语境中的存续与边缘化,也提示我们去追问:在国家叙事与地方实践之间,哪些劳作被记录,哪些劳作被遮蔽?对于笔者所关心的课题而言,战时造纸技术专家们的故事,或许是另一个层面的“看不见的劳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夹江手工造纸业的再考察,不只是对一个产业命运的补白,更是对现代中国工业化与知识生产多重逻辑的再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