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强评《伐木》|伯恩哈德的文人共和国

《伐木:一场情感波澜》,[奥]托马斯·伯恩哈德著,马文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3年10月出版,256页,75.00元
一
《伐木》出版于1984年,是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的晚期作品。一部典型的伯恩哈德小说。伯恩哈德的风格和主题通过该篇便可领略。
风格是不分段落的长篇独白,循环重复,讽刺谩骂。
那种“骂”还不是一般的尺度,而是恶语伤人,是脸色铁青的怨怼。其行文节奏的回环复沓,使得讽刺谩骂还具有一定程度的音乐性。也就是说,是一种旋律性、渐强渐弱、具有和声效果的言语攻击。总之,这种风格就是刺刺不休的愤世嫉俗。至少在奥地利文坛,没有人比伯恩哈德更为愤世嫉俗了。
主题是文人艺术家的生活情状,有关文艺圈的私语杂感,有浓厚的自传成分。作者写的是他熟悉的生活。
《伐木》发表之后招来麻烦,有人对号入座,起诉作者诋毁其名誉,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伯恩哈德的创作生涯中,此类事件发生过不止一次,或是被指控为玷污某个人的名誉,或是被指控为“侮辱国家尊严”。究竟是怎样的侮辱和诋毁,奥地利之外的读者,和作家不在同一个时代,会有些隔膜,那种言语的锋芒则是不难感受。
伯恩哈德的作品读来是有刺激性的,甚至会让人上瘾。讽刺文学总是会让一些读者喜欢而让一些读者不待见。讽刺文学向来都不是文学的主流,当代文学中这个种类尤其少见。《伐木》是一部地地道道的讽刺小说。

托马斯·伯恩哈德(1931-1989)
二
《伐木》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该篇讲的是不具名的主人公(即独白叙事人)参加朋友的葬礼,随后出席“艺术家晚宴”,晚宴至次日清晨散场,人们道别离去,故事也就结束了。
一篇意识流小说。独白叙事人坐在晚宴客厅的靠背椅上,冷眼旁观,评述他和晚宴主人奥尔斯贝格尔夫妇的关系,他和葬礼主角乔安娜女士的关系,以及他和宴会上其他几个人的关系。他思今忆旧,郁郁寡欢。
书中描绘了一个文人共和国,维也纳的作家艺术家组成的社交圈,其权力中心是由奥尔斯贝格尔夫妇等人所占据,他们有钱有名,有话语权和社交主权,是文化时尚的倡导者,艺术观念的教育者,阅读口味的裁判者。这种文人共和国,任何地方都有,规模不等罢了。《伐木》把上世纪八十年代维也纳文人的风雅或附庸风雅刻画出来,煞是生动。
例如,沙龙主人奥尔斯贝格尔夫妇,他们把聚众吃宵夜称作“艺术家晚宴”,还去书店购买流行的维特根斯坦著作,确实是蛮风雅。奥尔斯贝格尔是钢琴家,“韦伯恩的继承者之一”,几十年如一日充当“继承者”角色。再如,女作家珍妮·比尔罗特,“维也纳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自称其近作比弗吉尼亚·伍尔夫“前进了一大步”,也就是说比《海浪》写得好,“边说边点上一支烟,双腿交叉站立着”。
这些人在谈论易卜生的剧作《野鸭》,因为维也纳城堡剧院正在上演该剧,而晚宴主宾是出演该剧的一个名角儿,按照奥尔斯贝格尔夫人的说法,是“城堡剧院最伟大的、最富有个性、最具天才的演员”。这位“天才演员”直到午夜过后才来赴宴,让众人饿着肚子等候,而他到场后却对谈论戏剧艺术不感兴趣,只管低头喝汤。
一讲细节我们就知道,这篇故事性不强的小说是有料的。文人共和国和其他社交圈一样,细看之下还颇有看头,个个都是角色。
书中最有趣的是两个人,奥尔斯贝格尔和珍妮·比尔罗特。他们俩谁更有趣?应该是各有千秋。珍妮·比尔罗特抓住一切机会表现自己,年老色衰却风头不减,是那种势头一起来就再也压不下去的咄咄逼人的知识女性范儿,不容忍有一分钟受到冷落。
奥尔斯贝格尔也喜欢自我表现,是属于不可控、间歇性发作的类型;酒喝多了便口吐狂言,说“城堡剧院是猪圈”,还把他翘首以盼、在《野鸭》中扮演艾克达尔的名角说成是“狂妄自大、连台词都记不全的家伙”。他在晚宴上对夫人撒娇,仰靠在椅背上朝夫人“伸出舌头”。有一度还把假牙摘下来示众,嬉皮笑脸,乐此不疲。
奥尔斯贝格尔乐意扮演丑角,是孩子气的、轻浮促狭的、无政府主义风格的丑角。晚宴嘉宾、城堡剧院的“天才演员”,倒是像自矜自重的沙龙主人,他的风格是每说一两个单词就喝一口汤;“他说,艾克达尔,盛一勺汤,曾经是,盛一勺汤,我一直,盛一勺汤,最喜欢的角色,盛一勺汤”;“他还把简短的词语分开说,比如几十年,他说几十,盛两勺汤,然后再说年”。他用这种语气和节奏说话。
《伐木》从头至尾都是在展示叙事人(他也是一位作家)的观察。那双锐眼甚是锋利,把人们看不到或是看到也未必注意到的细节加以刺探。
他郁郁寡欢吗?是的,他很少言语,孤立在人群之外。他品尝笑料的方式表明,那种落落寡合的思想活动不乏消遣的乐趣。其实是不见得有什么乐趣,不过是无聊空虚罢了。但这种无聊空虚中至少还有讽刺的乐趣。
三
伯恩哈德笔下的文人共和国,多的是令人发笑的细节。喜剧性谐仿显得尖刻生动而不乏愉悦感(有天分的讽刺作家能够传递这种愉悦感),而其讽刺的力量是在于道德严肃性。所谓尖刻也是源于道德苛察,绝不拉低人格判断的水准线,冷嘲热讽,一个都不宽容,尽管这么做其实并不愉快。
《伐木》把一个绝非愉快的问题抛在读者面前:那些和叙事人一起成长、拥有艺术家气质和艺术家才华的人,为何到头来都失败了,而且变得不堪入目?
表面上看没有失败,除了自杀身亡的乔安娜,其他人都混得有头有脸,弹钢琴的还在弹钢琴,搞创作的还在搞创作,主办沙龙的还在主办沙龙。但从精神上讲,他们的存在是和理想背离,随着时光流逝变得越来越糟糕。叙事人说:
“他们所有人,如人们所说出了名了,成了所谓著名的艺术家,他们成了所谓艺术委员会成员,他们称自己为教授,登上许多学院的讲坛,时而被这所学院时而被那所大学邀请,他们时而在这个研讨会时而在那个学术论坛发表演讲”,而“他们还是一事无成,他们所有人都没有登上高峰,他们的所谓高峰”,“只不过是自我满足和自我慰藉”。
也就是说,年轻时确实是有艺术家的气质和才华,到了一定的时候,体内的小市民就占据上风,成了“伪艺术家”,成了那种实质一事无成的所谓成功人士。
珍妮·比尔罗特,“其作品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充其量是一种多愁善感的饶舌,或是浅薄的煽情”,而她“自以为可以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相提并论,甚至还超越了她”。
奥尔斯贝格尔,他那种“几乎是没有音调的”音乐“是地地道道对韦伯恩令人无法忍受的、毫无创造性的模仿”,“比韦伯恩贫乏和寒酸十倍、百倍”,和珍妮·比尔罗特一样,他“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有点才能的小市民”。
在叙事人看来,小市民本性就是问题的答案。作为个体艺术家和维也纳文人共和国成员,其特点无非是小市民习气。他们起点都不低,不是“韦伯恩的继承者”就是“奥地利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奥地利的格特鲁德·斯坦因”“奥地利的玛丽安·摩尔”,但他们选择了平平常常的发展道路,没有学到偶像的精神,只是学到一点形式的皮毛,与天才的观念和个性背道而驰,最终“陷入小市民那种精神粪窖里”,还一个劲儿地扮演成功人士。
对小市民习性的揭露和抨击是伯恩哈德作品一以贯之的主旋律。《伐木》的讽刺是尖刻的,和《历代大师》等篇相比未必是更尖刻。在《历代大师》中,哲学家海德格尔被说成是“穿灯笼裤的小市民”,其描写令人发噱,令人捧腹,除了伯恩哈德谁敢这么写。对维也纳文人共和国的清算是其小市民批判主题的一个分支。伯恩哈德每次提笔写作,都是在如饥似渴地重复这个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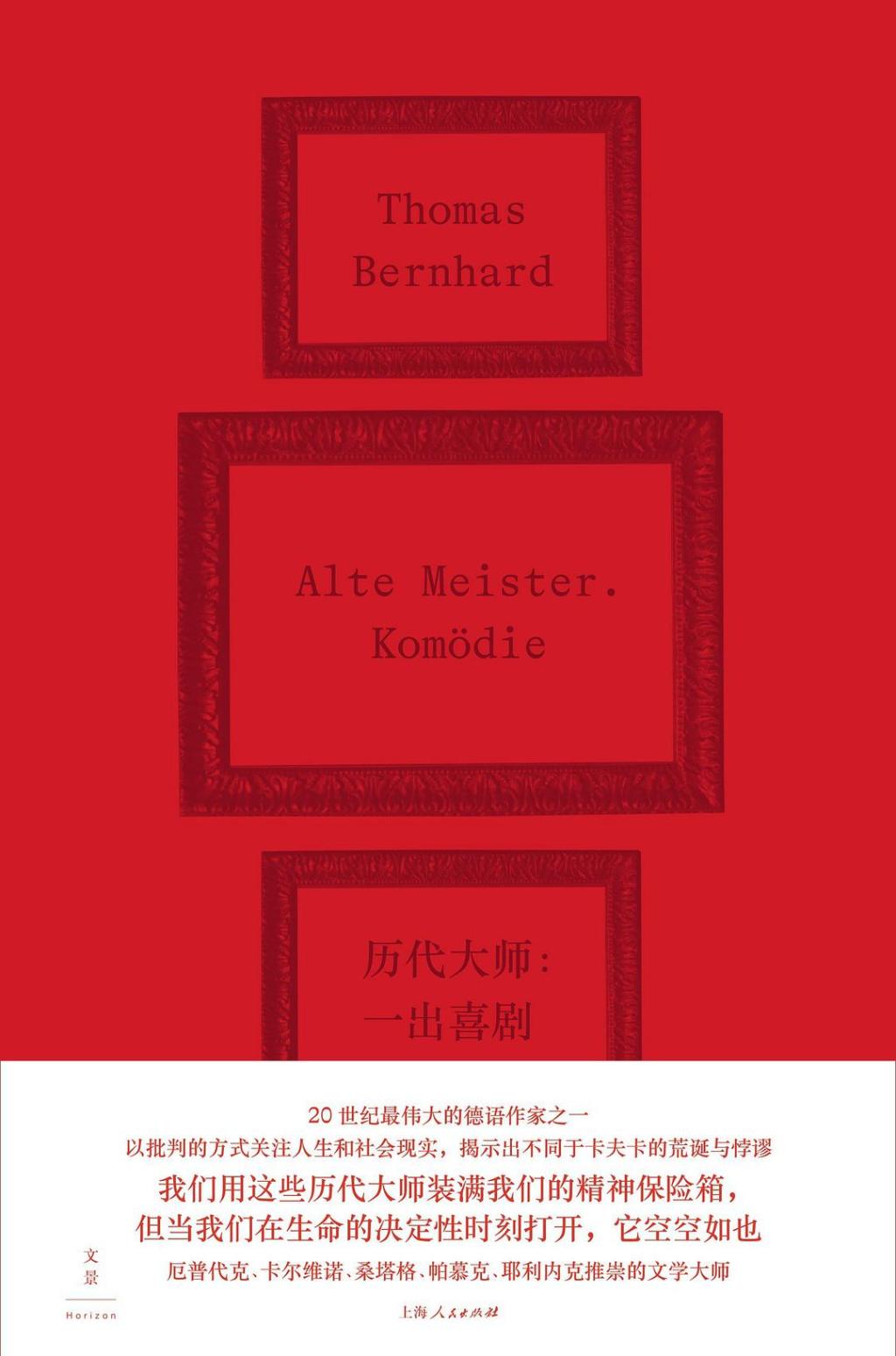
伯恩哈特著《历代大师》
《伐木》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意识形态,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三十年视为维也纳文人堕落的里程碑。以珍妮·比尔罗特和安娜·施雷克尔(“奥地利的玛丽安·摩尔”)为例,其堕落不仅是表现为艺术气质和艺术才华的日益衰退,更是表现为道德个性的腐化变质。叙事人指控道:
“五十年代,当时我才二十岁,她们称国家为平民百姓最根本的不幸所在,我得说今天仍然如此,但是她们在六十年代初就肆无忌惮地屈从于国家”,“把自己一股脑儿地出卖给了可恶又可笑的国家”,“公然巴结讨好国家机器,不仅是背叛了自己,也背叛了整个文学”;“最近几十年来,她们不放过任何机会,对她们一直贬斥和诋毁的国家,施展起随机应变、投机取巧的伎俩”。
也就是说,艺术精神让位于市民精神,这个过程标志着文人的堕落。
《伐木》的批判主要是针对两个方面,一是攻击小市民习性,一是抨击国家主义思想。作者认为,国家主义思想是意识形态的毒瘤,其实质是巧取豪夺;小市民本性则是此种意识形态的根基,其原则是投机取巧;而文化之都维也纳的败落,其文人共和国的庸俗嘴脸,便是一个写照。
那么,《伐木》的叙事人何以在晚宴上冷眼旁观,格格不入,而伯恩哈德的作品何以总是激起争议,让人觉得是在诋毁公民名誉,侮辱“国家尊严”,于此也就不难领会。
四
伯恩哈德让人想起法国作家塞利纳,《茫茫黑夜漫游》的作者,其风格化的语言是在表达怨愤、执迷、攻击和谩骂。奥尔罕·帕慕克在一篇评论中指出,伯恩哈德的创作有塞利纳的调门,此外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贝克特等人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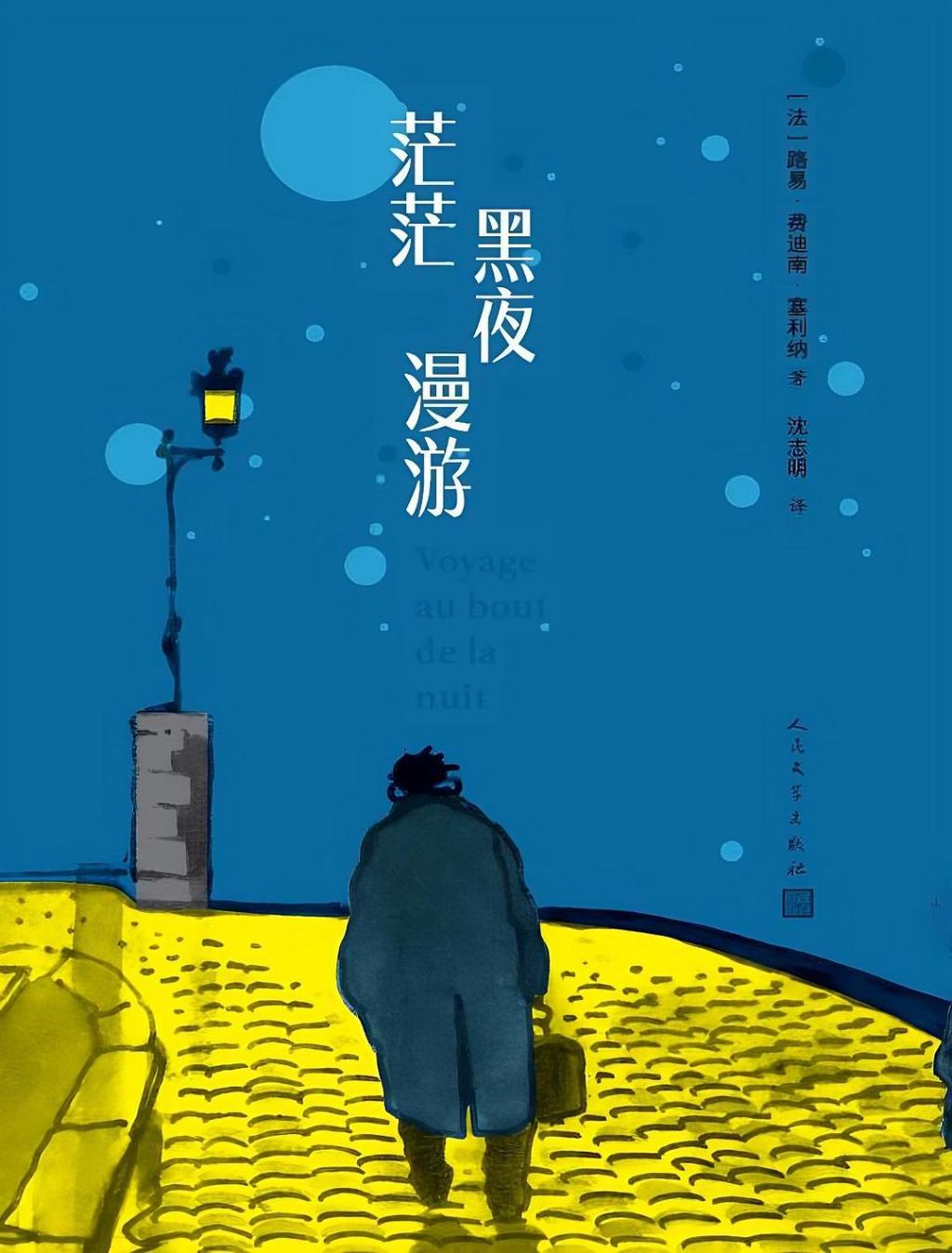
塞利纳著《茫茫黑夜漫游》
可以这样说,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倾向是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切地说是源于《白痴》(南江译)中的人物伊波利特。一个年轻的病人,肺病患者,具有病态的敏感和狂热;一个聪明人,怀疑造化弄人,认为上帝把优秀生灵制造出来,目的就是为了毁灭和嘲笑;他躺在床上消磨时光,盯着窗外的砖墙,思考着上帝、虚无、绝望和自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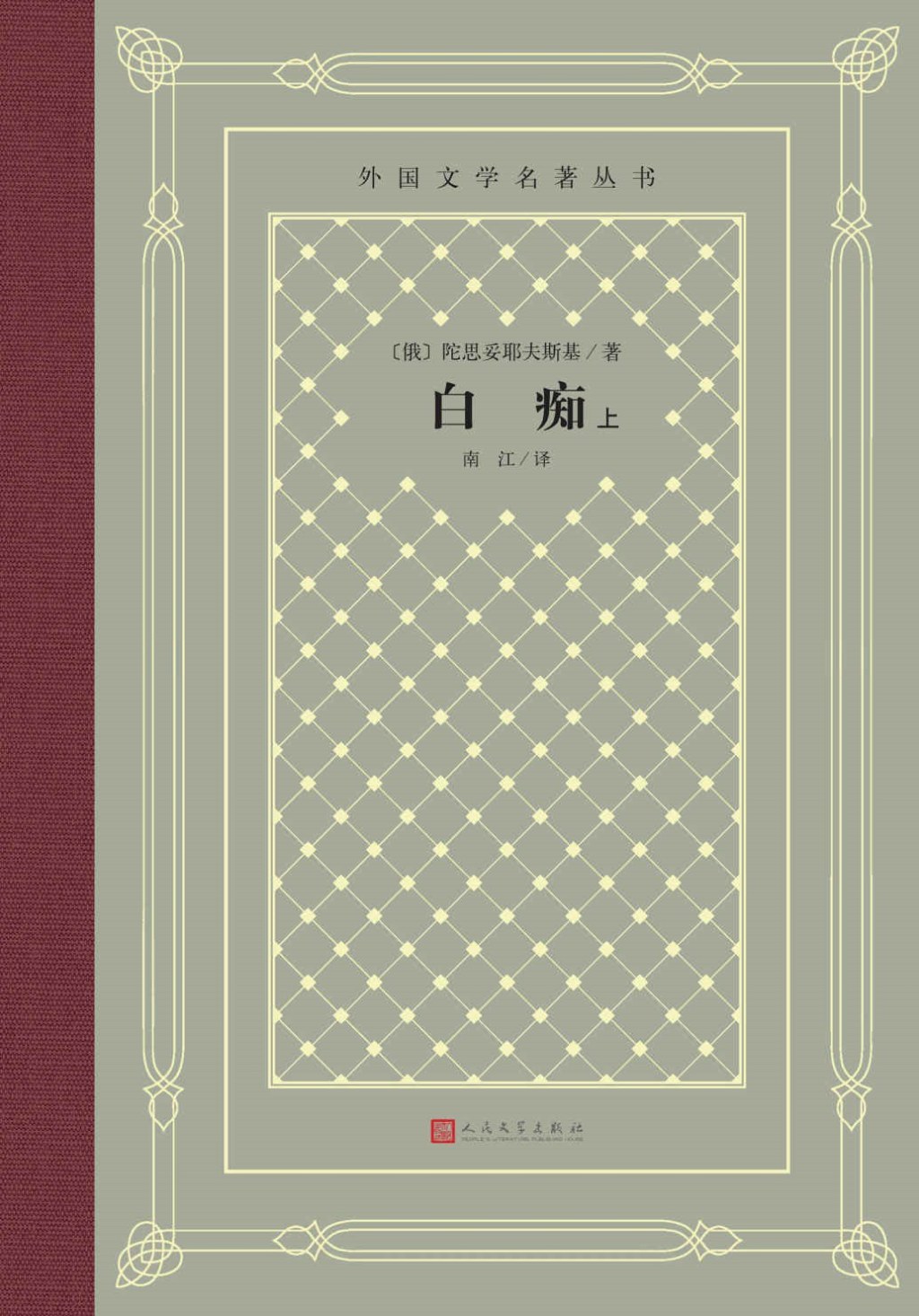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白痴》
伊波利特的无尽的怨诉,就是卡夫卡、贝克特等人习用的语言。他凝视的那堵光秃秃的墙壁,便是荒诞哲学的自我阐释的背景板。他对梅什金公爵的尖声叫骂,仿似塞利纳、伯恩哈德等人的高调怨怼。伊波利特喊道:
“我恨你们大家,你们大家!您,您,您这个口蜜腹剑的伪君子,白痴,乐善好施的百万富翁,我恨您超过恨世上的一切人和一切东西!”
伊波利特站在梅什金公爵(耶稣基督的化身)的对立面,最能够表达其怀疑主义的立场,或者说反映其苦涩而怯懦的自尊,一种病态的清醒和怨恨。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这个人物,在作家的创作中有其同类(《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伊凡等),而且代表了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族类,即所谓的虚无主义人物谱系;我们从卡夫卡、贝克特、塞利纳、纪德、萨特、加缪等人的作品中均可看到其直系后裔,或是相似的面孔和形象。
提及这一点是为了便于观察伯恩哈德的小说,其叙事人的形象属性及其在欧洲文学中的定位。
《伐木》和《历代大师》等篇的叙事人的独白是发生在一个极其逼仄的空间,约等于伊波利特的枕头和墙壁之间的距离;卡夫卡的《地洞》、贝克特的“无名者三部曲”也是如此,在高度压缩的空间中说话,分享一种既像是神谕又像是牢骚、既像是演讲稿又像是私房话的语言。
这种虚无主义时代才会有的独白语言,是一种神经质的语言,其独特的魅力也在于高度神经质。在《伐木》中我们看到如下两方面的表现。
其一,叙事人出尔反尔的心理戏码及其效应。
如前所述,晚宴上的文人艺术家个个都是角色,叙事人施展讽刺作家的笔触,把他们当笑料来写。其实,叙事人的行为也不乏可笑之处,某种程度上是在扮演丑角。一方面他鄙视奥尔斯贝格尔夫妇,决意和这对夫妻以及维也纳文人圈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一方面又欣然接受邀请,去参加他十分厌恶的“艺术家晚宴”。
“我竟然闪电般地、痛痛快快地接受了邀请,我其实是应该理智些,谢绝他们的邀请。”
“一个刚强的人,一个有性格的人,我想,就拒绝他们的邀请了,但我既不刚强,也不是那种有性格的人,相反我是一个最懦弱、最没有性格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会听从任何人的摆布。”
叙事人出尔反尔的心理戏码,比那种对象化的客观讽刺更具有喜剧色彩。这种描写也是最接近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风格;它把神经质的分裂的自我暴露出来,使人格的统一性弱化,而且在理性层面上自相矛盾,出现一种感伤、气恼、多愁善感的倾向。《伐木》的戏剧性并不是仰仗故事情节,而是基于这种自我分裂的语言。
可以说,一个反英雄的丑角,一个自我肢解的痛苦的人,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臧否同类,因为他自己就病得不轻;他和文人共和国不是一种客观对立关系,而是自我意识的冲突,对小市民性格的高调抨击也是这种自我斗争的反映;他首先必定是解剖自己,肢解自己,评断自己,在一种苦恼意识的驱使下才对他人进行讽刺、谩骂和抹黑;也就是说,其言行是基于一个理性的反思的自我,却始终是陷于阴暗和绝望。但唯有深刻的苦恼意识才能够培育这样一种东西,将骄傲和怯懦、冷静和善感、执迷和嘲谑集于一身。《伐木》的自我分裂的语言体现一种深刻的喜剧性。
其二,伊波利特式的空间及其效应。
《伐木》的讽刺是尖酸的,从头到脚都是在挖苦、泄恨。但该篇也不乏善感的忧郁情调。对死者乔安娜女士的描写便流露这样一种情调。
乔安娜是篇中唯一没有受到讽刺的人物。她是来维也纳打拼的外乡人,颇具艺术才华和实验精神,但在婚姻和事业两方面都遭到重创,孑然一身,穷困潦倒,最后上吊自杀。叙事人对她的遭遇寄予同情。
如果说奥尔斯贝格尔夫妇、珍妮·比尔罗特等人的堕落是归因于不可救药的小市民劣根性,那么乔安娜的悲剧是出于什么原因?
是丈夫的背叛和伤害,是维也纳这个大都市的冷漠无情,是痴迷艺术、不擅长自我经营、沦落底层而走投无路;总之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悲剧。在叙事人看来,她的才华以及精神的纯粹都值得敬爱。
乔安娜的插曲,其哀戚的情调是和叙事人的讲述分不开。叙事人那种循环往复、此消彼长的话语,是在伊波利特式的空间里展开,具有回音壁的声效,而这种声效是在扩展一个孤儿心理的巨大空洞。所谓伊波利特式的空间就是孤儿心理的空间,其空洞的声效是在凸显世界的荒芜和冷漠。
在孤儿的心理空间中,乔安娜成为叙事人的同类。也就是说,悲剧本来会有多种解释,没有一个因素是可以忽略的,而在叙事人的讲述中,被遗弃的孤儿形象却成为悲剧的中心意象,它凝结着叙事人的生活体验和世界观,即对边缘人物的同情,对底层生活的记忆,对意识形态(国家主义、实利主义等)的控诉,对文化艺术的追悼。乔安娜的故事变成了一曲挽歌。
《伐木》的叙述清醒、冷酷,却不乏伤悼的气息。
这其实是一个伤感的故事。不仅是乔安娜的插曲有这种情调,奥尔斯贝格尔夫妇、珍妮·比尔罗特等人的滑稽剧也有抚今思昔的伤感。叙事人当年是奥尔斯贝格尔夫妇的小跟班,是珍妮·比尔罗特的弟子和密友,他从他们身上获得文学艺术的启蒙和教养,但眼下却是形同陌路、格格不入。
将近三十年过去了,故事里的人物变成了老人和死者;维也纳文人共和国衰朽败落,物是人非;“有天分的写作者变成令人作呕的所谓国家艺术家”,“从模仿他人写作的少女作家变成模仿他人写作的体态发福的高龄女士”,而这一切怎能不让人伤感!
《伐木》的副标题“一场情感波澜”,就是指这种文人心态的特定倾向的爱恨情仇。叙事人割袍断义,划清界线,但是界线又岂能消除得了。他的自我意识和苦恼意识离不开维也纳文人共和国;他的骄傲和绝望、伤悼和迷思是专属于这个地方。作为残余的理想主义者和另类的怀疑主义者,他的身份是通过他所厌弃的文人共和国定义的。
五
简要解释一下书名。
《伐木》让人以为是要写高山林场的故事。读完小说,觉得内容和书名并无关联。
中译本第224页、第225页上,城堡剧院的“天才演员”说了一番话,大意是:人如果在自然环境中而非在这种人为环境中出生和成长,那就要健康得多;“走进自然,在那里呼吸,把那里看成是自己真正的、永久的家园”,“那是最大的幸福”;“森林,乔木林,伐木”,那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环境,完全不同的生活。
这番话引起叙事人的共鸣,认为是包含“老年的哲思”,让无聊的“艺术家晚宴”朝着睿智的哲学思维发展。《伐木》的书名是从这个细节提取的,要给阴暗压抑的叙述注入一点启示的微光。
在另一部小说《沉落者》(马文韬译)中,叙事人谈到啤酒运送司机(另一种环境里成长的人民和普通劳动者)时,他说——
“我们总是想象我们与他们坐在一起,一辈子都感到被他们吸引,正是这些所谓普通的人,我们对他们的想象自然与他们的实际不符。我们一旦真的与他们坐在一起,就会看到他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切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我们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同类”;“像我这样的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坐到人民的桌上吗,这是不可能的”,“像我们这样的人,早已经不可能与人民坐到一张桌子上”,“自然像我们这样的人总是向往人民的桌子,但是我们坐在那里不合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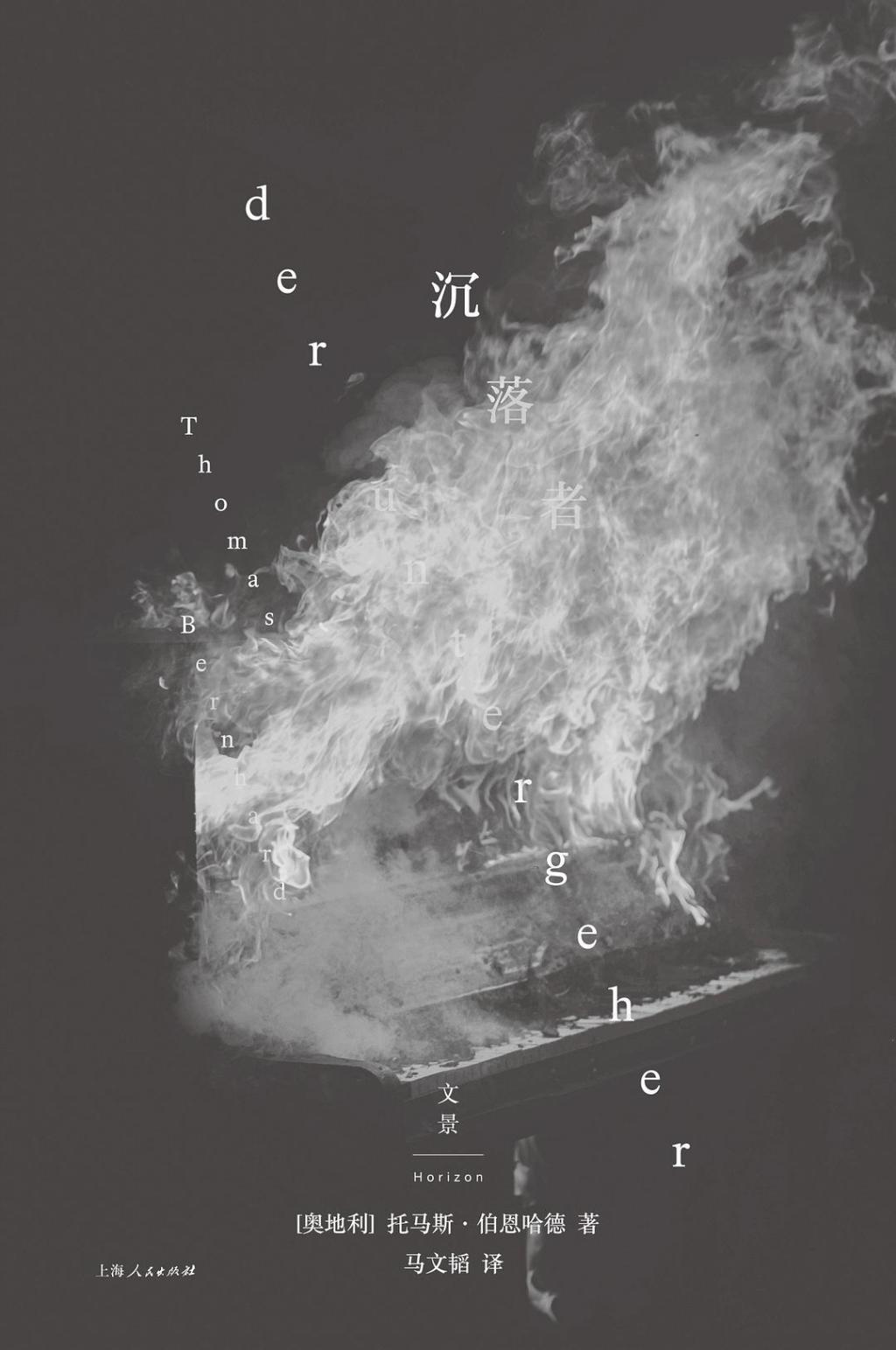
伯恩哈特著《沉落者》
《沉落者》中的这段话就像是对《伐木》的一个补充或反诘,意思是说:晚宴上的颓废艺术家真的“走进自然”,与伐木工人为伍,怕也不见得能够融入其中;文人终归是要跟文人在一起,属于他们那个报团取暖但也相互倾轧的文人共和国,而“森林、乔木林、伐木”的念叨则是一种祈愿,用乔伊斯的术语来讲是代表某个时刻的顿悟(epiphany),不过是悲观主义思想的一种暂时性的休克。
伯恩哈德是一个把文人气质、文人群体写深写透的作家。他是小市民出身,其精神则根植于德语文化传统,叔本华、尼采的传统,德奥音乐文化的传统。他对小市民习气的批判,他的愤世嫉俗和自我孤立,代表着这个传统的遗存,是回光返照式的一种激活。小说家当中只有他是这么做的;可以说,他是一个写小说的叔本华或维特根斯坦。
《伐木》是一部讽刺小说,特色是在于讽刺语言的运用。不过,其真正的特色是“将疯癫和风趣结合”的风格,这是伯恩哈德和卡夫卡、贝克特等人的一种关联,体现现代主义文学特质。疯癫和风趣的结合,在“自传四部曲”和《维特根斯坦的侄子》等篇中表现得更充分,堪称是伯恩哈德诗学的精髓。
伯恩哈德的自传色彩浓厚的小说叙事人,在不同作品中重复同一个角色;他是神经质的文人,凄凉的孤儿,愤怒的复仇天使;他熟谙市民心理,洞悉时代精神,以精湛的语言操控着思想利器和文化密码,在伊波利特式的空间中扮演着无名大师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