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逝世五十年|托马斯·迈耶:她在你身后把门关上

海报设计 祝碧晨
汉娜·阿伦特是投身于行动的思想家,也是当今被引用最多的政治理论家之一。她关于极权主义、恶的平庸、人的境况、沉思生活的思考,在二十世纪影响深远,如今更愈发成为我们理解当下动荡世界的思想源泉。
今天是汉娜·阿伦特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日。德国慕尼黑大学(LMU)哲学专业特聘教授托马斯·迈耶(Thomas Meyer)此前在上海接受了《上海书评》的专访。迈耶研究政治哲学,他2023年出版的德文版《汉娜·阿伦特传》(Hannah Arendt: Die Biografie)在学界和传媒广受赞誉,是首部基于档案研究写就的阿伦特传记。迈耶也是阿伦特著作德文校勘版全集(Hannah Arendt: Kritische Gesamtausgabe)主编。最近,他的《汉娜·阿伦特:二十世纪思想家》(Hannah Arendt: Die Denkerin des 20.Jahrhunderts)中译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本次访谈中,迈耶分享了他通过档案发掘出的阿伦特巴黎流亡岁月的故事,探讨了阿伦特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复杂关系、她对哲学与政治的理解、她的感情生活和写作风格,以及她与海德格尔、施特劳斯等人的思想纠葛。

《汉娜·阿伦特:二十世纪思想家》,[德]托马斯·迈耶著,强朝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索恩2025年11月出版
目前有两部阿伦特传记译介到了中文世界:一部是伊丽莎白·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的《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另一部是萨曼莎·罗斯·希尔(Samantha Rose Hill)的《汉娜·阿伦特》。当您的德文版传记于2023年出版时,同期面世的还有林赛·斯通布里奇(Lyndsey Stonebridge)的《我们有改变世界的自由:汉娜·阿伦特关于爱与不服从的教诲》(We Are Free to Change the World: Hannah Arendt’s Lessons in Love & Disobedience)。谈谈您的书与其他传记的不同之处吧。
托马斯·迈耶:汉娜·阿伦特的形象承载了许多故事,而这些故事几乎完全建立在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的传记基础之上。扬-布鲁尔是阿伦特的弟子,也是唯一一位在阿伦特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的人,两人关系密切。1975年12月4日阿伦特去世后,其遗产的管理者们——包括作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阿伦特的私人助理洛特·科勒(Lotte Köhler)以及她在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助手杰罗姆·科恩(Jerome Kohn)——在小范围内决定,应由扬-布鲁尔来写这部传记。因此,在阿伦特的文件按其遗愿被运往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之前,他们给了扬-布鲁尔独家查阅权。扬-布鲁尔能够接触到阿伦特所有的朋友,听他们讲述阿伦特青年时代的故事,其中自然包含了她与导师马丁·海德格尔和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关系,以及她在巴黎的岁月等等。
但一切都基于阿伦特的著述和这些流传的故事。其中一些故事后来衍生出了各种版本,它们与《爱这个世界》一起,共同构建了一个阿伦特的形象。我对这些故事并不满意。我认为它们恰恰构成了对阿伦特本人的遮蔽,进而使那些与她生命血肉相连的著作也变得模糊不清。我走访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档案馆探寻事实。我发现,许多广为人知的故事都带有一种将阿伦特神秘化的倾向。所以我写了一本新传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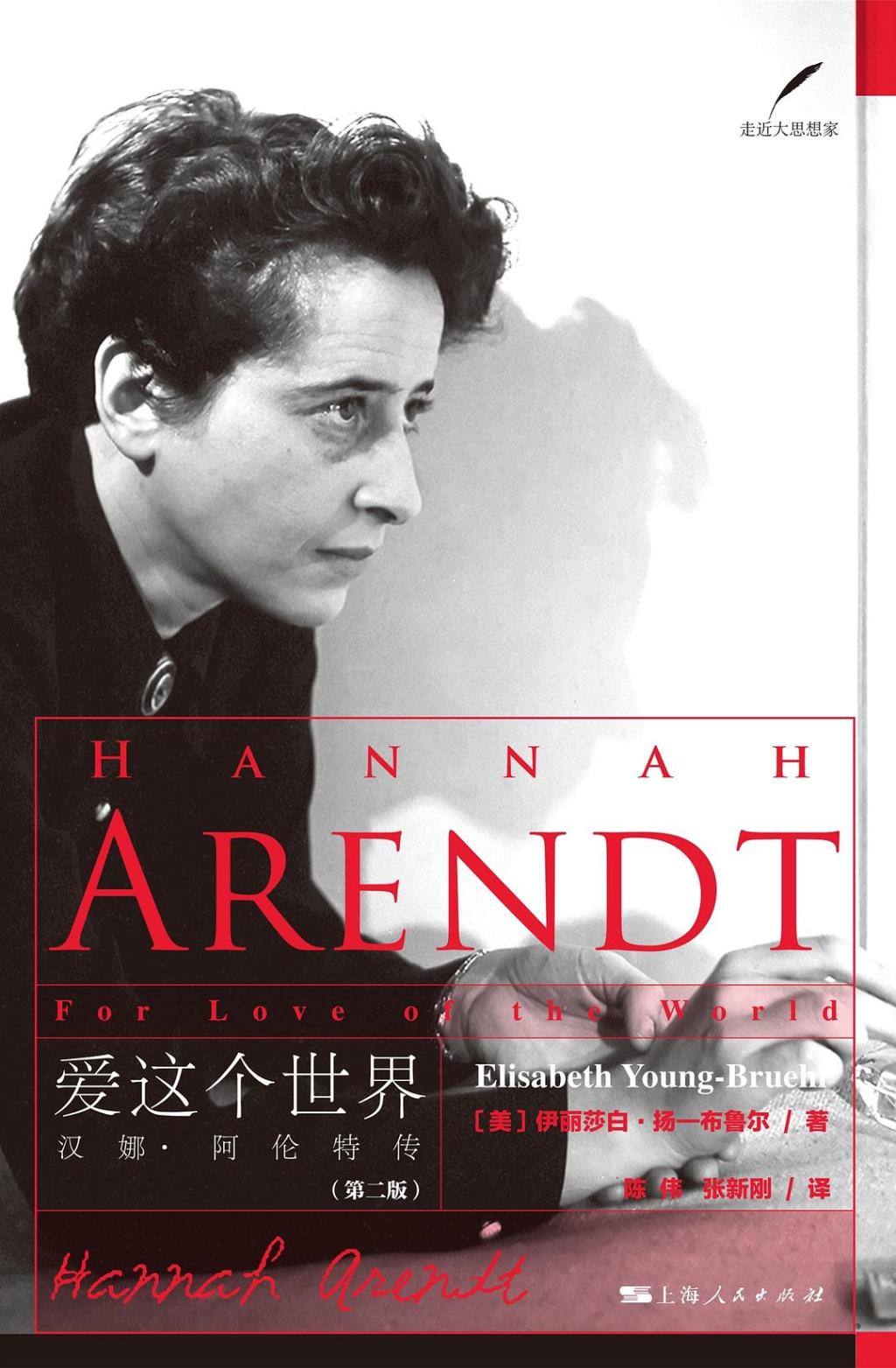
伊丽莎白·扬-布鲁尔著《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
我对严格的时间顺序不感兴趣,因为汉娜·阿伦特本人对此也不感兴趣。当你细读她的代表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你会发现全书的三个部分并未遵循时间线索,而是构成了一种复杂的混合体。所以,叙述至1955年,我暂且落笔,为传记的第一大部分画上句点。彼时,四十九岁的阿伦特已定居美国,确立了自己作为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她心智已成,此后的所有著作,皆是基于这一成熟心智的产物。我想,在1955年之后,继续沿用时间顺序叙事已显得意义寥寥,我便转而探讨那些我深感兴趣的议题。我用了很长一章写作为媒体人的汉娜·阿伦特,写阿伦特与女性主义,写她与导师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的哲学关系。我还用了一章探讨她后期著作的不同方面。
我以一种完全异于通常传记的组织方式来编排这部书,这是一种冒险。一些抱有既定期待的评论者对此感到愤怒,他们无法接受这种写法,但我并不在意。也许世界上没有一本书是完美的。至少我将这部传记视为我个人的贡献,而不是像扬-布鲁尔的书那样——尽管她的书出版四十年了,至今仍被许多人奉为了解阿伦特生平的《圣经》。对于我这样一个观念史学者来说,这简直愚不可及。歌德曾言:每一代人都必须书写自己的历史,因为每一代人所处的环境皆不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是柏拉图或康德的教诲,也并非现成的真理,我们必须重新诠释经典,去发现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殊异洞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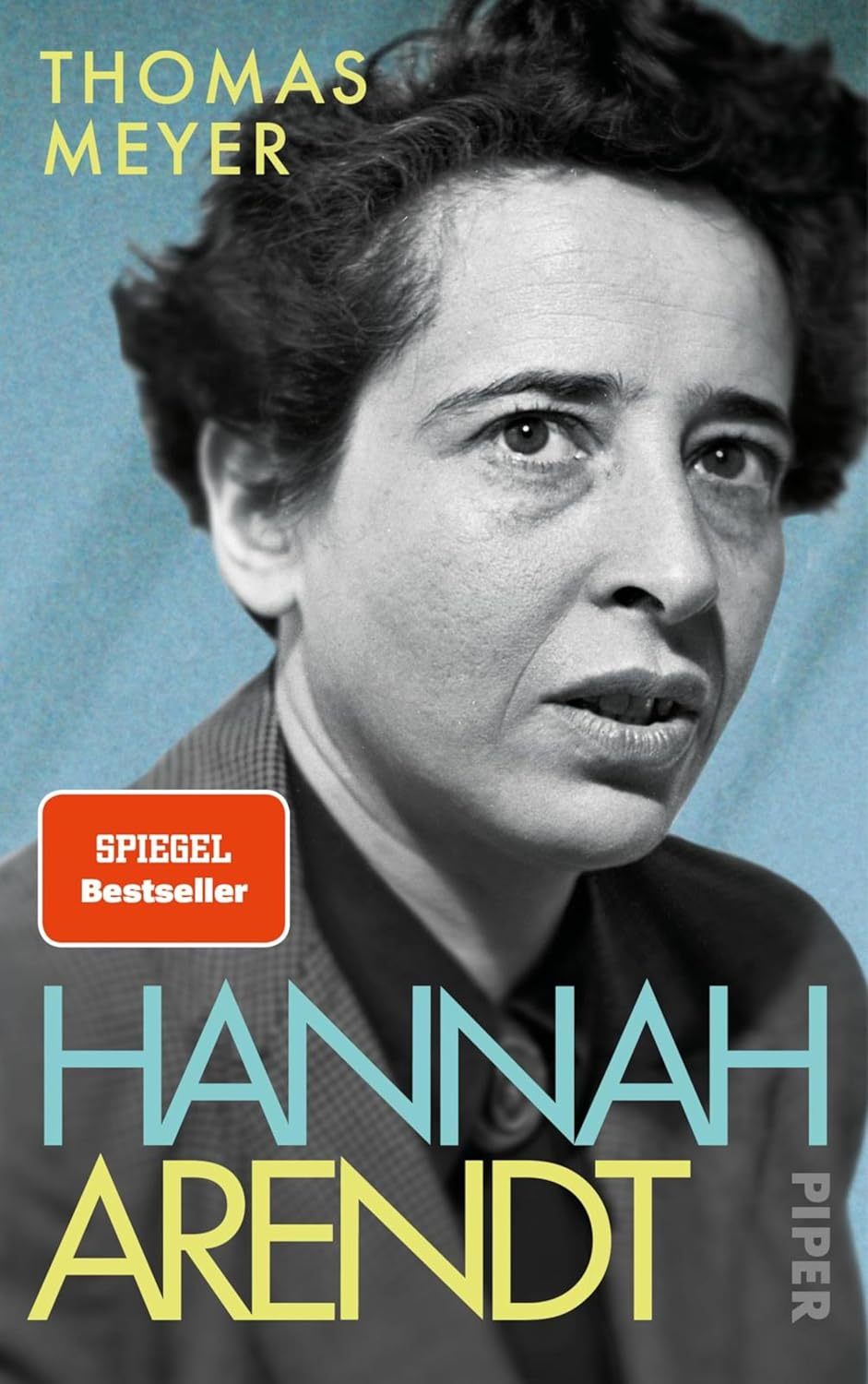
托马斯·迈耶著《汉娜·阿伦特传》
您从档案里收获了什么新发现?为什么过去没有人关注这些档案材料?
托马斯·迈耶:哲学家、政治学家,包括许多传记作者,根本对档案研究不感兴趣。即便有兴趣,他们也往往满足于阿伦特本人的陈述。档案研究通常与历史学家相关,而我本人是哲学出身。哲学家们难免认为关于知识分子的历史信息并不重要,只有著作本身才重要。阿伦特的老师海德格尔曾在讲座中说:当你想了解亚里士多德的生平时,你只需要知道他出生、工作,然后去世。这就是你需要知道的关于传记的一切。
至于我的书有何新意?首先,我重构了一部全新的阿伦特家族史。依托多地档案,我将其家族脉络上溯至十九世纪初。这段跨越约两百年的历史不再基于道听途说,而是建立在我挖掘出的、关于柯尼斯堡(Königsberg)犹太社区的坚实历史文献之上。其次,对于她1933至1940年的巴黎岁月,我提供了一份截然不同的叙述。基于在耶路撒冷和哈佛大学档案馆的新发现,我认定这六年是阿伦特生命中最具决定性的时期。当时,她服务于一个犹太组织,投身于营救十四至十七岁青少年的工作。关于这项行动,此前仅有零星传闻(罗斯·希尔虽有提及,但也仅止于此)。可以说,我在此处的浓墨重彩,确实构成了对过往传记的一种批评——它们大多流于泛泛,缺乏深入洞察。我的传记将具体回答:她究竟与谁共事?在何种环境下工作?明年我将与以色列海法大学的同仁合作出版专著,首次完整刊布关于阿伦特巴黎岁月的原始文献,并附以长篇导言与评论。

1933年的阿伦特
根据您的发现,阿伦特在巴黎帮助了一百多名犹太儿童逃离纳粹迫害,前往巴勒斯坦。您怎么看阿伦特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关系?为什么她后来与犹太复国主义分道扬镳?
托马斯·迈耶:问题的症结是,我们掌握的信息越丰富,想要界定或理解阿伦特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关系反而越发困难。流行的说法是这样的:1930年代纳粹上台后的数日牢狱之灾,让阿伦特意识到了其犹太身份的政治意义。出狱后,她经由布拉格和日内瓦流亡巴黎,在当地,她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工作。然而,1941年移居纽约后,她成为该运动的激烈批评者,发表了《再思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 Reconsidered)一文,从根源上对其进行猛烈抨击。随后的1963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更是让她被扣上了“自我憎恨的犹太人”的帽子。我要给笃信这个故事的人泼一盆冷水:这连一半的真相都算不上,实际的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
当然,这一叙事首先是由阿伦特本人在1964年接受德国记者君特·高斯(Günter Gaus)那次著名的电视访谈中确立的。这段访谈在网上可以找到,有数百万人(我想也包括许多中国观众)都看过。她在采访中说,她与犹太复国主义没有瓜葛。她之所以曾向犹太复国主义者靠拢,仅仅是因为他们是那时唯一采取行动反抗纳粹的人。遗憾的是,这位出色的记者并没有追问她,她参加的那个犹太组织“青年阿利亚”(Youth Aliyah),它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在希伯来语境里,这里的“阿利亚”意味着“浪潮”,它是用来统计从不同国家、族群涌入巴勒斯坦(以及后来的以色列)的一波又一波移民潮的。

阿伦特接受高斯采访
因为阿伦特的话总被奉若圭臬,人们至今还沿袭了这个叙事。在我看来,那一时期的阿伦特当然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否则该组织不会允许她加入。而且她必须向法国政府及其他官方机构表明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成员。当你阅读那些信件时,她在那里呈现的无疑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身份。她还在1935年去过巴勒斯坦。这些是已知的,但不为人知的是她在这个组织中介入得有多深。
阿伦特生命中还有第二次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关系密切的时期。有一个成立于1940年中期的名为“犹太文化重建”(Jewish Cultural Reconstruction)组织,在战争一结束便立即行动起来,派遣人员前往东欧,寻找幸存者、犹太会堂以及这些社区的文献。阿伦特是这个组织的协调人,她与老朋友、来自耶路撒冷的学者格尔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紧密合作,他俩当时就是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起工作的。

阿伦特在卫斯理大学
这个复杂故事还有最后一段。大约一年前,我偶然发现了一本书——阿伦特在1958年与其他十六位专家合著了一本关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书。这完全不为人知,有些专家甚至否认她参与此事。想象一下,这个十七人小组,尝试为这个持续存在的冲突寻找解决方案。当然,他们必须处理犹太复国主义问题,团体中的一些人本身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
至此,我们还能轻易说阿伦特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吗?我认为不能。关于这个问题还有更多可说的,但以上是她在一系列发展中的主要节点。
阿伦特后来对哲学家和知识分子的看法,对哲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是不是也深受巴黎岁月的影响?
托马斯·迈耶:阿伦特与君特·高斯的访谈里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她真的生气了。她说,1933年后,许多朋友对希特勒产生了非常复杂、特别的想法,“他们想到了关于希特勒的一些极其聪明的事情”(Es fielen ihnen furchtbar kluge Dinge zu Hitler ein)。这意味着他们确实对德国的事态发展有很多思考。当然,背景是他们想确保自己与发生的事件保持距离,但同时又或许在寻找某种原因或解释。从那一刻起,阿伦特就将“知识分子”这个词与“不负责任”联系了起来。知识分子立场不稳,他们随波逐流。他们对真理不感兴趣,却非常在意自身的际遇。
说回巴黎。1933年也意味着阿伦特与哲学的决裂。因为那些通常自认为是真理持有者、认为哲学全然关乎真理的哲人们,对纳粹运动缄口不言。或者他们像海德格尔那样为之喝彩,发表支持纳粹的演讲。对阿伦特而言,他们未能经受住时代的考验。他们没有反对这场运动,或者至少去分析这场运动,而是成了机会主义者,甚至更糟,成了纳粹政权的一部分。既然如此,她为何还要继续从事哲学呢?替代性的选择是政治生活,这意味着直面自己作为难民的生存状态。她是一个被自己的人民——德国人驱逐出国家的人,她曾是德国公民,但从1933年起便不再是了。这就像有人对你宣布,你不再是这个共同体的一部分了。哲学未能提供对这一境遇的理解。当然,回到古希腊悲剧,你可以找到描绘难民处境的篇章。在文学和哲学中存在着难民叙事传统,但在当时的特定情境下,没有人激活这一传统。阿伦特没有抱怨,而是转向了政治行动主义:开讲座,发表演讲,与青少年一起工作,摒弃哲学,转投历史学和社会学,为的是理解自己的生存境况,理解犹太人——她的人民的生存境况。

1961年耶路撒冷,被告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
在我看来,此时哲学甚至不在她兴趣的第二序列。她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有一些哲学的孤岛片段,但整本书是关于反犹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的历史-哲学分析。你可以从哲学角度去阅读它,你会发现有几页关于霍布斯的讨论(她根本不是霍布斯专家),还有对马克思、现代资本主义及暴力兴起的分析。但这些都不能归到传统意义上的哲学论述。没有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可能有点康德和霍布斯,仅此而已。如今被归在阿伦特名下的《康德政治哲学讲稿》,是她去世后出版的,她从未打算出版一本关于康德的书。而且她对康德的解读也很难说是主流的。
阿伦特在难民组织的实践中发展出了“拥有权利的权利”(right to have rights)的观念。您认为这个观念在当今全球难民政策的讨论中仍有启示吗?
托马斯·迈耶:“拥有权利的权利”或许对今天的世界更为重要。如今有数百万的无国籍者,数百万人虽名义上享有权利,却无法行使这些权利。因为没有法庭和法官,法律就毫无意义。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形是,所谓的国际秩序显然无法影响政治发展。我们本拥有这些工具:以前联合国能向爆发危机的地区派遣部队,将敌对势力分开,确保人们至少每天能获得水和食物,让儿童、妇女、老人生存下来。然而,如今即便是在如此低限度的层面上,我们也没有充分实现“拥有权利的权利”。我脑海中不断浮现的是“纸老虎”这个词。我多么希望阿伦特这个著名的表述能更贴近当今现实。但我们看到全世界灾难频仍,世界秩序丝毫没有给这种概念留下空间。顺便一说,阿伦特一度对国际法非常感兴趣,因为她必须与国际法、国际机构打交道来为孩子们获取签证。巴勒斯坦在当时是英国的托管地,限制非常严格。
或许是基于档案的缘故,您这部传记的语调几乎始终是冷静中立的。但在写到阿伦特生命中的男性时,您却显露出评判的姿态:您反对她与海德格尔的关系,至于与她共度大半生第二任丈夫布吕歇尔(Heinrich Blücher),您似乎认为他是个在智识上远不及她的风流之徒。能谈谈阿伦特的感情生活吗?它们是否影响了她的其他思想?
托马斯·迈耶:可以说,人们对于后来的纳粹党员海德格尔与犹太人阿伦特之间的关系,抱有一种近乎迷恋的好奇,视其为某种神秘而引人入胜的存在。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两个伟大的头脑因为一段恋情而走到一起……我真的不关心这些。每个人都可以购买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通信,自行判断,构建自己的故事,甚至把故事搬上银幕。
阿伦特是一位现代女性。她并不认为只有男性才能更换伴侣,那是一种非常自虐且带有负面意义的传统观念。她在不同时期拥有过不同的伴侣,某些时刻,这些关系或许是重叠的。没什么大不了,这就是现代生活。然后她和哲学家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结了婚。那段时间,我认为她并不真正快乐。但这又怎样?我们在感情关系中都有过不快乐的时光。然后他们离婚了。这也不是阿伦特的什么创举。

汉娜·阿伦特与第一任丈夫君特·斯特恩(后以君特·安德斯为笔名),1929年左右。
再后来她嫁给了布吕歇尔。他是个风流成性的人。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阿伦特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甚至有些天真。或许她以为丈夫背叛这种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她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能看出,他作为非犹太裔,却对犹太女性有执念,所以他的许多情妇都是犹太人。这伤害了阿伦特,因为至少其中一段婚外情是和她的一个密友罗斯·费特尔森(Rose Feitelson)。她没有慷慨大度到愿意接受开放式关系,作为浪漫主义者,她依然愿意相信一心只许一人。阿伦特可以没完没了地讨论别人的外遇,但对于她自己的个人生活,则另当别论。

阿伦特与第二任丈夫布吕歇尔
现在有趣的问题是:这是否对她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影响?如果有,又是如何影响的?《人的境况》里有一个理论,行动是不可预见的,行动总意味着承担风险,我们不知道在某一情境中,以及之后会发生什么。不过当我们去爱,当我们被背叛,这些都是非常私密的事,我们不应将它们带入政治,我们需要一个私人领域。正是私人领域的存在,让公共领域得以成为政治性的空间。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通信被公开并非出于预先计划,而是由于美国有学者率先刊布了若干信件片段,这才促使家族决定编辑出版完整的通信集。我认为,阿伦特非常注重不将政治与私生活混为一谈。如她在与高斯的谈话中所说,去爱你的朋友,那是存在于朋友与她之间的友谊,那不是政治。
流亡使阿伦特成为双语作者。用两种语言写作对阿伦特意味着什么?
托马斯·迈耶:我是十二卷阿伦特德文著作集的主编,我们即将出版最后一卷。国际学界很少引用德文版本,但它们是阿伦特思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我甚至会说那是更真实的部分。与此同时,她为美国公众写作。她意识到英语并非她的母语,所以她必须翻译。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她的最后一本书《心灵生活》(Life of the Mind),两卷都是用英文写成的,那也是一次尝试。
说她所有其他著作都存在两个版本并不准确。她的大部分书都是自己翻译的,但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翻译,而是重新思考、重写。在我看来,即使不是完全改动,它们也是不同的书。我认为,阿伦特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因语言之故,而同时栖居于两个不同世界的哲学家与政治思想家。德语对她而言,引用德国诗人海涅的话,是“随身携带的故乡”。她说德语的地方,就是她的祖国。这也意味着一种德国传统。她在接受高斯采访时说,变疯狂的不是德语,而是德国人。语言对她来说,至少是部分免受纳粹污染的。

五十多岁的阿伦特在花园里
阿伦特认为,孤独感是极权主义的本质经验。在当今这个高度互联却又充满社会疏离的数字时代,阿伦特对孤独感的分析,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极端主义的泛滥?
托马斯·迈耶:孤独只是极权主义的一个方面。你还需要极权主义的环境和各种要素。极权主义当然是一个非常辩证的概念:一方面是被孤立的、孤独的个体,另一方面,极权主义政权鼓动人们加入一个由其主导的集体。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论及暴民(mob)的一章,有一段著名的讨论,指出政权对集体生活的控制与孤独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
我认为数字化世界正在模仿这种概念。你坐在地铁或公交车上,刷着短视频,当你喜欢某个视频时,就可以发送一颗心。发送一颗心,这曾经是表达爱意最深刻的方式。那需要直接的关系,需要凝视对方的眼睛,或许还要有鲜花相伴,以及“我想把余生都交给你”这样的经典告白。而现在,人们却在不断重复这个动作:动辄就发一颗心。你真正表达的是什么?人只有一颗心,或许可以有不止一位伴侣,但每天几十次地发送爱心?与此同时,你还与其他人分享,你会发表评论,他人也会回应,从而构建起一个社群。但这社群可能转瞬即逝,而你却持续不断地重复这一过程。同时你还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必须遵守规则。这种个体性的分裂状态很有意思,它未必是坏事,至少可以说,我们的意识被训练得能够适应不同的情境。虚拟世界需要的托马斯·迈耶,不同于坐在教室里的那个,不同于与妻子相伴的那个,也不同于世界上与其他公民共处的任何一个。这些托马斯·迈耶之间如何产生联结?是否正因为我的碎片化状态——或许因此我更脆弱——操纵我会变得更容易?这些问题愈发引人深思。
阿伦特在《心灵生活》和《人的境况》中,包括在《政治中的谎言》(Lying in Politics)与《真理与政治》(Truth and Politics)这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中,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所有这些影响,即使是以自我反思的模式存在,都无法被忽略或避免,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现代个体似乎认为,自己应当全天候地接受来自我之前描述的那些不同世界的所有信息。而我并不认为这种传播方式真的有助于我们相互理解,成为真正的人。

晚年阿伦特
您早年研究过列奥·施特劳斯,写过一篇《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诸起源》(The Origins of Leo Strauss's Political Philosophy)。您认为施特劳斯与阿伦特的“政治”概念之间,是否存在亲缘性?能谈谈他们的联系与差异吗?
托马斯·迈耶:首先,他们彼此认识。1920年代中期,两人曾在马尔堡大学相遇。有传闻称施特劳斯曾爱上阿伦特,但遭到她的拒绝,因为她认为他是个犹太裔纳粹,原因是他与纳粹理论家卡尔·施米特有过往来。当然还有另一个更著名的轶事。1956年,阿伦特受邀发表沃尔格林(Walgreen)系列讲座(这些讲稿两年后集结成《人的境况》一书)。当时她站在电梯前,而她的报告厅与列奥·施特劳斯授课的教室恰在同一栋楼里。于是施特劳斯与阿伦特在电梯前相遇,他发觉身旁正是阿伦特,便招呼道:“你好,汉娜。”她回应道:“你好,列奥。”仅此而已。这段轶事至今仍为阿伦特与施特劳斯的门生们津津乐道。

列奥·施特劳斯
但正如你所说,事情当然不止于此。两人都对城邦(polis)着迷。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德国移民群体的痴迷。耶鲁大学的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刚写了一本关于冷战自由主义者的书,他说这些人都痴迷于城邦和希腊思想,因此他们甚至无法提出一个连贯的现代自由民主概念。我在此不想讨论莫恩的观点。但无论如何,城邦是西方最古老的人类共同体秩序。如果我们认为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就必须回归城邦,以理解人类共同体的组织何以成为可能。阿伦特和施特劳斯都发现,所谓的“古典政治哲学”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瞥之见,让人们得以理解如何组织国家生活、等级制度、各层级之间的关系等等。用埃里克·沃格林的话来说,这就是世界秩序。
但两人的分歧就此显现。在阿伦特看来,这种施特劳斯主义的分析得出的是一种政治哲学的政治概念,因其无法与现代生活产生联系,所以这是一种自我隔绝。施特劳斯所构想的政治生活,仅适用于那些已然属于——或渴望跻身——哲学圈层的少数人,即从施特劳斯视角认定的真理持有者,那些最具深刻洞见者。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的理念。我对此并无贬斥之意。其本身颇具启发性,让我们得以深入理解哲学性政治思维的结构。
但对阿伦特而言,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表现。我们身处世界之中——可以说,这是施特劳斯从未接受过的概念。并非因为它是海德格尔式的概念,而是因为他认为我们必须过一种哲学的生活。这也正是哲学家必须做的事:创造一个哲学思考的领域。思考不仅仅是思考——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同意阿伦特——但它与现代生活无关。因为现代生活关乎行动。这里我们看到了主要区别。施特劳斯最后出版的一本大书,讨论的是柏拉图的《法义》,他在书名中使用了“行动”(action)一词。但这完全是另一个概念,指的是作为政治哲学结构的城邦中的行动。对阿伦特来说,特别是在1945年之后,这不过是哲学家的幻梦,完全是一种人为的观念。对我来说,有趣的是,在中国,施特劳斯和阿伦特对知识分子群体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您看来,中国读者应该从哪里开始阅读阿伦特?您怎么看阿伦特的写作风格?
托马斯·迈耶:我先给自己做个广告,你们可以读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的我的这本小书,接着读伊丽莎白·扬-布鲁尔传记的中译本。我在中国遇到了非常优秀的阿伦特诠释者,比如《人的境况》的译者王寅丽、《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译者安尼。

王寅丽译《人的境况》
那么从哪里开始进入阿伦特的著作呢?我推荐《人的境况》。通过这本书,你能接触到那个成熟而真实的汉娜·阿伦特。高斯的访谈总是一个绝佳的起点,可以看到她的言行举止,看她吸烟的样子,感受她在公共领域的风采。然后,我想读者会自然而然地发现更多文章,比如收录在《共和的危机》里的作品。我相信读者。

1944年,阿伦特斜倚凝思,手中夹着香烟。这张照片由流亡摄影师弗雷德·斯坦恩(Fred Stein)在纽约拍摄。
阿伦特所有的书——这或许是我对她风格的看法——没有一本书是为专家而写的。除了她那篇关于奥古丁的博士论文(由于拉丁文与德文混杂,即便对德国人而言也近乎天书,这是当时的惯例),其余作品皆非专为学者所作。同时,她的书也绝非给初学者准备的入门读物。这种做法在学术写作中实属罕见。她所立足的中间地带极为复杂。你很容易被书开篇的精彩故事引入门径,但随后她便在你身后关上了门,使你全然沉浸于她的思想世界,难以脱身。她的文本组织方式极为精妙,融合了分析、观点与引述,迫使读者在跟随她的过程中不断自我提升。最奇妙之处在于:当你合上书本时会感叹“读阿伦特原来如此轻松”,她比施特劳斯好懂得多。但这种轻松感(easiness)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太容易因此低估她的思想深度。我想这正是其独特之处。
目前不少中文版本的阿伦特著作都译自英文。也许有一天会有人从德文翻译,届时我们将读到的是不同的书吗?
托马斯·迈耶:我正与一些中国学者保持联系,他们未来会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坚信,下一波,也就是中国关于阿伦特的研究文献及作品译本的新浪潮,将会同样基于德语版本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