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证明或反驳「一个红色的物体,当没有人看它的时候,它依然是红色」?

我觉得很神奇……怎么没看到有人提第二性(secondary quality)的。
第一性 -- 第二性的区分(primary–secondary quality distinction),如果不是来源于 John Locke,至少也是因他而被西方哲学的导论性课程所提及。
第一性(primary quality)是物体固有的属性,比如说,质量(mass)、电荷(electric charge)、数量(number)、……——这些玩意儿放在当代物理的语境下是没有太大争议的。而如果我们用传统一点的词汇,则会有类似于广延(extension,大概指实体占据的空间?)这样的玩意儿,可能会稍微有点争议,不过问题应该不是太大。但是这里最终会引出一个 scientific world 和 manifest world 的区别。[1]
第二性(secondary quality)是依赖于人的感官的属性,比如说,颜色、气味、味道、声音、触觉。我不确定疼痛和本体感觉(自体感觉?proprioception)诱发的那些,不太好描述的属性算不算。我的手疼,算不算我的手具有疼这个属性?我感觉我的手(臂)是伸直的,或者,弯曲的——不是通过看的方式看到,而是通过我内在的感觉感受到这一点,这算不算一种第二性?对于后面这个问题,可以参考《身体性自我知识初探》[2]和《身体性自我知识再探》[3]。
(Remark on extension 广延. 在当代物理学视角下的尴尬之处在于,从一个亚原子层面的视角看,日常的实体,比如说一个金块,尽管是在日常意义上是致密的实体,但实际上大多数地方都是“空”的,我们感受到的体积多半都是由电磁力造成的斥力。也就是说,广延性看上去又像是一种第二性:如果我们是一种以发射和接受高能粒子束来感受所谓的广延的生物,我们对于广延的把握可能会依赖于我们发射的粒子束的强度。我们的穿透力越强,就能感受到越多的“空”。而凝聚态物理也告诉我们,more is different——这和下面 Lock 对于第一性拥有 divisibility 的表述也是冲突的。
哪怕我们说,电子或者夸克有体积,我们一方面不能证明这个体积是不是真的存在,还是说,仅仅是另一种斥力,另一方面,它和我们日常意义上的广延相去太远了。维护这种更进一步微观结构上的广延相当于把日常意义上的广延完全取消掉。End of remark)
(Remark on divisibility 可分性. 在 Locke 的意义上,primary quality 似乎有某种 divisibility:一个可分的物体,被分割之后,体积(和)保持不变、质量(和)保持不变……但是这似乎和当代凝聚态物理背道而驰:more is different。当然,我们可以凝聚态物理来反驳这种对于 primary quality 的刻画,但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哦,那凝聚态物理里面那些东西就不是 primary quality。当然,除此以外还有第三条路线,这就像是说,一个圆无法分成两个半圆:“圆”性不见了。 ——如果我们认为“形状”是一种第一性的话。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延续了第一性的这一层精神的,其实是量子力学里面那个“全同性”:基本粒子是不可分辨的。我们无法分辨这个电子和那个电子。——这个程度的东西对应的性质,可能算是一个真正的“primary”的玩意儿。一堆电子是完全“对称”的(大概,我说错了不要打我),你只能挑出特定的数量,而不能挑出具体的哪个是哪个。而更高一层的复杂结构还算不算 primary,我觉得随便吧。End of remark)
总体来说,我们想说第一性存在于物质自身,而第二性依赖于主体。这些话都是非常含混的。什么叫做存在于物质自身?什么叫做依赖于主体?
抛开漫长的哲学史,让我们来看一点现代的人话。
第二性,一言以蔽之,就是这样的玩意儿:[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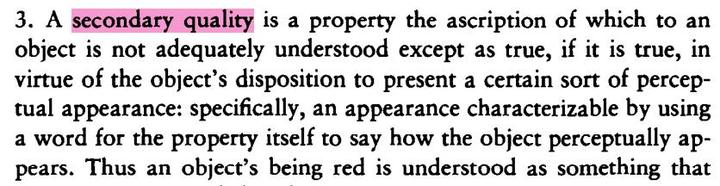
当我们将第二性,比如说“红”这个属性(property),归于(ascribe to)一个对象(object),比如说,“这个苹果”的时候,是在说,这个苹果有对认知主体(比如说我)展现出特定感觉表象(也即,主体,即我,因此看到红色的感觉)的倾向(disposition)。并且,主体描述这个对象的词汇,借助的恰好就是描述(characterize)我们感觉表象(perceptual appearance[5])的这个词:红色。
(Remark on color blindness 色盲. 毫无疑问,如果一个人是完全的盲人,那他很不幸,无法在我们这种意义上充分理解(adequately understand)苹果的红色这种第二性。但是,对于色盲,其实这个措辞也比较微妙。所谓的“看不见红”不如说是“红和绿看上去一样”,或者“看不见它们的区别”。于是,对于色盲群体来说,不是看不见,而是无法分辨对于一般人来说的,两种不同的第二性。这个地方或许存在一个裂缝,但是我不知道要如何弥合它。起码,它不是第二性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感觉经验和语言之间的问题,而更进一步,这个地方的问题可能会和所谓“色谱反转实验”、“黑白玛丽实验”更接近一些,所以我暂时不想考虑它。End of remark)

请注意,这里有两个稍微有点儿不同的玩意儿:我看到的红,和归于对象的红。前者是我的经验,而后者是我对于对象的认知。后者是这个苹果的第二性。而前者,其实和这个苹果的距离要远一些。从因果的意义上来说,是这个苹果使得我感到红,这没有问题,所以我不能说“我看到的红和这个苹果完全无关”。但是从 recognition 的角度上来说,我可能根本没有对这个苹果的 recognition:比如说我是透过一个小孔看到这个苹果的红,而根本“看不到这个苹果”——这里的解读是 de dicto 意义上的,而从 de re 的意义上,我当然看到了苹果,只不过我没有认出这个苹果是苹果罢了。你看,从 de dicto 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无法说“我看到一个苹果,并且我认不出它”,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可能在将作为第二性的红归属于这个苹果的情况下,认不出这里有一个苹果。——距离大概在这里。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我这里用了“苹果”和“对象”之类的词汇,但是时间依旧是一个需要考量的因素。对于问题所说的情况来说,这里并没有做出回答。因为当我们说归于某个对象的时候,更准确的说法是,归于这个对象在被我们观察期间的切片。就像是说,我们说,这个苹果现在是红的,或者,这个现在的苹果是红的。——它似乎没有对更加广泛的苹果,比如说,过去和未来的它做出承诺。
有人会认为,这个地方的 disposition(倾向)表示的是这种承诺:也即,即便我没在看,或者,没有人在看,它也是红色的。我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想把它作为一个绝对的规律,那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些瑕疵。这种瑕疵会使得我们不得不将表述弱化。
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某种电子设备,只有在有光照的情况下会显示出特定的颜色。比如说,没有光照的时候,它就是黑色的。(不是因为没有光照而不反光,而是真的变色,以现在的科技其实不难做到这一点)而当我们能看见它的时候,它才变成红色。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里的 burden 其实和 Hume 用图片(电影也是一张一张的图片)的方式怀疑因果关联的方式类似:我们的确可以承认 Hume 所说的那种情况可能成立。我们也可以承认这里有这种奇怪的东西,但是我们恰恰是建立了一个新的链条。我们可以设想的是一个基于别的因果链条的替代情况。重点在于 the need for laws is undisputed——不管是约束人的法律,还是“约束”自然的自然律。
我们对于第二性的把握必须以一种恰当的方式进行:比如说,我们对于作为第二性的红色的恰当把握依赖于看到红色,这个地方强调“看到”,而不是别人在手心写字告诉我它是红色,或者,别人通过说话,口头地告诉我它是红色,又或者我触摸盲文知道它是红色。但是不仅如此,我或许能够通过倍率极高的电子显微镜观察其微观结构“判断”出它是红色——依旧是一种“看到”——但是并不是我们这里认可的看到。
如果你觉得上面这个“微观结构”的说法有点蹩脚(确实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至少可以在黑白显示器上查看数据,分析它的反射光谱,然后知道它是红色的——但这也不是我们把握第二性的那种看到。
重复:我们对于某个对象的第二性的把握,必须在该种 第二性 以恰当的方式 呈现在 我们面前 的时候,才能把握第二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物理检测算是 off topic。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相信了一些东西,物理属性的“不变”才是“证明这个东西一直为红”的有效标准。而不能反过来说,用物理上的不变来“证明”第二性是不变的。
实际上这个可以拔高为一个物理主义随附性论题:
- 没有物理上的区别,就没有心理上的区别。
这个地方有两个直接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是一个无法辩护的主张,而是一个“信仰”,如果题主把问题滑落到这个层次,反对这个,那我似乎没什么可以说的了。
其次,物理上的区别本身当然有,你在
时刻看苹果,
时刻没看苹果,
时刻看了苹果。你想说没有物理上的区别?时间都不一样了你说啥呢?所以你要用一些更高级的抽象概念,至少把前述描述中的“时间”给抽象掉,引用更高级的假设,比如说某种“时空平移不变性”(我不确定叫不叫这个),把某些东西打包入一个 class 或者一个 type 中,然后说这个 class 或者 type 中的特定 property 不会随着 class 或者 type 之外的成员(如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A lot of burden.
一个粗鄙的例子:两个可能世界中,同一个人的物理状态可能是一样的,更具体一点,有完全相同的脑结构,看到了完全的视觉输入,但是可能世界
中这个人面前的是一个假苹果,可能世界
中,这个人面前是一个真苹果。由于这两个人的物理状态完全一样,所以有些人想说,他们有完全一样的心理状态,比如说,他们都相信这是一个真苹果,于是说“我看到了一个苹果”——但是这句话在
中错误,在
中正确。这当然不是在反驳“心理状态”和“物理状态”如何如何,而是在问:我们打包的时候,要如何保证打包的东西是一个不变量,比如说“这个人脑袋中有特定的想法:我看到了一个苹果”。也即,我们怎么保证我们选出来的,被打包的玩意儿是的确只和自己有关的?——至少第二性从一开始就不像是这种东西。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关于一个物体自身的东西,都可以和它之外的东西无关。而要怎么把这个地方说清楚,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当我们已经有了量子力学之后。
对应题目的情况,考虑一个更加怪异的,暂时性的 spectrum inverse:当每个人闭上眼睛的时候会经历一个 spectrum reverse(不是黑变成白,而是别的什么,比如红绿、红蓝、红黄对转),也即,此时,这个闭着眼睛的人如果能看到东西,那么颜色将会是反转的。这个东西本身在物理主义者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出现什么物理层面上,比如说脑神经的突变,但是我觉得这不算一个证明)但是它以一种更加微妙的方式展现了如何绕过“想象某种电子设备,只有在有光照的情况下会显示出特定的颜色”中电子设备的物理性,把困难又丢回了 qualia 这一 hard problem 的一侧。
问题来了:丢开物理主义者,对于这样的人,我们重构一个这样的问题:当我闭上眼睛不看这个苹果的时候,它还是红色的吗?按照前述的设定,它此刻似乎不具有对我呈现红的 disposition:因为我经历了一个 spectrum inverse,所以此时如果我能看见苹果,我看到的不是那个红色的它,但是如果我睁开眼睛,它就变回红色的了——这是我内在的变化,而不是苹果有什么问题。——你测量苹果也没有用。喵啊。
至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谁他妈在乎呢?丢一边去就行了。因为我根本不相信这个构造(什么他妈的叫“这个闭着眼睛的人如果能看到东西,那么颜色将会是反转的”——实际上最后一个有效的反例,你必须要绕过“眼皮”之类的机制,而进入到一个很后面的地方,你可以想象一下这里有多困难,我懒得写了),而具体的“解决”也不会促进怀疑论者真正放下这个问题,而是会促进他们用一种更加精巧的方式回避掉你的解决方案。
回到问题本身,这里似乎有一个量化错乱那样的玩意儿——我不确定算不算量化错乱,但是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以数学为例,我们经常用先天性(apriority)来刻画数学:数学知识不依赖于经验。
但是,这个地方的“不依赖”是什么意思?从直观上来说,就是:数学知识不需要科学实验去证明。我们当然可以用数实物的方式确定一个加法式子,比如说 2+3=5 成立——你把两个苹果和三个苹果放在一起,数出来 5 个——这姑且算是一个“证明”。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数学不需要这种形式的证明。
但是如果一个认知主体(只是姑且这样一说)根本没有任何经验输入,没有任何感觉,那么,它何以可能习得数学?我们对于数学的学习虽然依赖于想象力,但是首先我们要有基本的,时空概念,然后才有可能学习数学。而我们甚至无法想象这个所谓的“认知主体”算得上是一个认知主体。
当然了,有些人可能会说一个电脑也可以学会数学。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层次的问题。这就像是说,一个沼泽人[6]不是一个生命,但是一个基因工程或者什么什么操作设计出来的生命则还有是生命的可能性 —— 一个没有“任何经验输入”的电脑“会”的那个数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依照人类的目的派生的。它的经验“继承”于人类的经验。而他实践出来的结果,也是由人类的解读保证的。就像是 AI 虽然目前能作画,但是依旧是我们在判断“这算一副不错的画”“这他妈也算画?”cf. 狗屁不通文章生成器。
而没有认知,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去更正它,某种意义上来说,“调参”都是不允许的。那还搞个犊子。
如果一个认知主体就是没有任何感知能力,它何以可能——别说拥有先天(a priori)知识了——称得上是一个主体呢?
这个数学上关于数学概念在何种意义上“不依赖于经验”的问题,和借由题题目的问题联想到的一般性的问题:抽象的“红”在何种意义上不依赖于具体的红的物体,在我看来,有类似的结构:我们的不协调感来自于一个全称量化:如果一种第二性(不是这个第二性的某个具体例子,而是它的哪怕任何一个例子),从来都没有任何人观察到,那么我们如何确定它存在于我们的概念空间 / 理性空间(conceptual space / space of reason)中?
(Remark. 当然这里不能跳太快,我更想说的其实是下面“神色”这种情况,而不是 Hume 说的那种,给我们一系列由深到浅的蓝色,其中空了某个位置——哪怕这个位置的蓝色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在人类面前,我们依旧可以(合理地)给它一个名字。
但是何种意义上来说是合法的?这就像是说,我们可以把元素周期表一直写下去,写到或许 120、130 乃至 150…… 又或者说,对于元素周期表里面已经有的那些元素,我们可以给它们“造”各种各样的同位素……或许量子力学会告诉我们,“其实它们都是合法的,只不过某些存在的时间太短”罢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随便吧。End of remark)
考虑一个这样的颜色:“神色”。这种颜色只有开了天眼的人可以观察到,比如说二郎神用第三只眼能看到,所有普通人都看不到神色——那么,神色存在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地用奥卡姆剃刀的原则说“神色不存在。”——请注意,我们仅仅是“可以说”。这里的本质问题在于,用康德的话来说,我们无法建立某种“objective validity”(当然,我怀疑我这里是瞎几把用概念,所以康德专家不要太生气)。——我们当然可以用“神色”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实际上在说什么——不是说完全不知道,我们当然知道“神色”是一种颜色,并且,只有原则上不存在的某些神话生物,如二郎神,可以通过第三只眼看到这种颜色——OK,这些部分我们都理解——但是,用维特酱的话来说,这不是知识,是设定或者说规定。康德会抱怨这里没有给出一个 deduction(福尔摩斯 / 康德的意义上)of the objective validity of the concept ``神色''。试图问神色存不存在,是对于理性能力的僭越——我们没有办法把理性能力伸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事实上这里已经极度简化了问题,对比一下上面红绿色盲的那个图,其实图中根本没有典范的红色,但是在多了,或者说,少了一类视锥细胞的意义上就是能产生如此大的“视觉差异”)
这个地方也不能一下子退缩得太厉害了:我们承认人是万物的尺度,又或者,至少在这里,我们的确需要人作为标准,但是这个标准不一定是我,或者我们。比如说,对于红绿色盲而言,虽然他们看不出特定颜色的区别,但是他们一方面有神经上的证据,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实验证明正常色觉的人有这种能力。所以,的确我们不必非得有特定的东西才能接受特定的概念。但是这个时候,它们就的确仅仅是概念,而不是直观。第二性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亲知的第二性知识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通过概念呈现的——它们是通过直观呈现的。语言里面有很多超越我们直观的东西,作为单纯的概念存在。我们没看过的动物,没吃过的食物,没听过的声音,它们当然可以存在,但是对于一个没有接受过这些对象的直接感官刺激的主体来说,这些概念无法 adequately understood。有些人能看到第四种颜色,我理解这个事情,但是无法把握她们把握的那种第二性。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至少在日常语言的意义上这样说:如果世界上从未有过任何人看到任何红色的对象,不管是因为物理上的缺陷,还是因为人眼的结构问题(比如说所有人都是红绿色盲),那么,至少在我们的概念空间中,红色就不会存在。事实上,对于很多原始部落的人,即便他们视力没有问题,也有可能因为语言中缺少绿色和蓝色的概念而缺乏对于这些颜色的分辨力。
——有人可能会着急、跳脚,因为这里的不存在其实有一个更加微妙的问题。这是我们在想象语言,所以会遇到想象力抵触:“但是实际上我们有红啊!它怎么可能没有呢?”这个想象力抵触的问题我也谈过了。[7][8]
甚至,我们可以问一个面向未来的问题,如果哪一天,我们进化了,或者,突变了,看到了新的颜色,不再是三种视锥细胞,看到的基础的不是三原色,而是五、六、七原色——怎么办?
——这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不是说我无法把握它的字面意义,而是没法给出回答:古人想象不到电脑,更加想象不到 cookie 和 cache 这些概念。语言不是语言自身,而和一整套生活方式相关。我们在这里,如果有分歧,是因为我们对于想象的生活方式有分歧;如果有想象力抵触,因为我们已经以我们所在的生活方式来使用语言;如果我们难以想象,是因为我们难以想象那种生活方式。——这些都是 OK 的,也是正常的。这些可能性都放在这里,我无法挑选其中哪个是正确的。
别说想象成为一个蝙蝠是什么样子或者想象四色视觉了,你不给我红绿色盲模拟器,我也不可能想象红绿色盲是什么样子的。谁他妈能想象出来在红绿色盲眼里老虎的颜色是如此之好的保护色啊?
但是题主显然不是在问这种 global 的情况。我们这个世界上有红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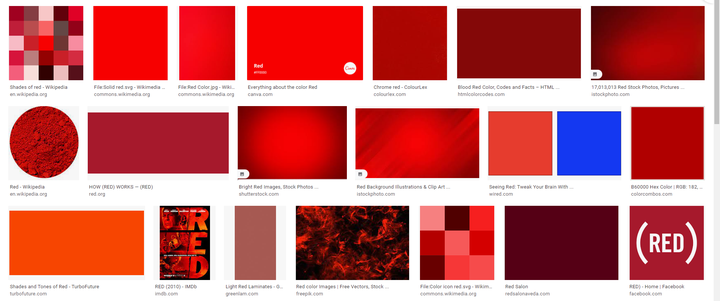
我们(非常抱歉,这里暂且排除了失明、红绿色盲色弱以及其它相关可能性的人)可以对于所谓的红色的概念有一个基本准确的把握。红色存在!
但是对于个别对象,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前面我们说过了,物件的“红”是一个派生的用法:虽然从因果链条上,是红色的对象使得我们看到红色,但是当我们把红色归于对象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抽象的颜色,红,的概念,然后才把它归属于一个对象。(正如数学先天性的那种反转: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需要经验,而实际上使用的时候又有一种超越性:我不再需要小孩子拿着比色卡那样来帮我判断上面那张图片里面哪个是红色,哪个是蓝色。——你一眼就认出来了。至于红色和深红和黑色,则是另一个问题了,比如说我想叫那个 25 等分图中最后一行中间的颜色黑色,或许你觉得它只是某种深红,这是模糊性的问题。)
我们默认,或者说,假定世界具有某种齐一性(uniformity)。这似乎并不是需要“提”出来的假定——我们太过于习惯如此这般看问题了。而反过来,如果有非齐一的情况,我们反而会认为这个地方需要有原因。
当我们谈及物体的颜色的时候,一个默认的感觉是这样的:物体不会变色。这里的不会,姑且设定在一个“突变”的意义上。苹果是红色的,什么意义上?至少在附近这个时间区间上。但是,
- 往前看足够远,它还未成熟,所以不是红色的。
- 往后看,它烂掉了也不是红色的。
——我们知道原因,我们可以给出生物学意义上的原因,但是这不是“我转头过去不看苹果了,它还是红色的吗?”引出的问题。甚至我们可以给出一些粗鄙的理由,比如说:我把苹果皮削掉了,颜色突变了,虽然它还是刚才那个苹果,但是它不是红色的了。——这虽然有点奇怪,但是也没有问题。它皮被削掉了嘛——这就是那个“变色”的原因。又或者,它被我喷漆了,喷成黑色的。——你看,我们都能理解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有原因的。“变”才是需要解释的,“不变”不需要解释。——至少日常思维模式是这样。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在日常意义上提问,说,你怎么保证……不会变色?我的回答是,不需要保证。但是,如果你是在某种不断拔高的怀疑论的意义上去问,那我他妈当然不能在哲学意义上保证。
日常的情况下,如果那个地方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把它放盒子里,盒子里也没有老鼠,那么正常情况下,它应该可以保持一段时间是相同颜色的。所谓的相同当然不是非常严格意义上的相同,或许会有肉眼无法察觉的变色产生,但是日常生活不支持我们做出这样的区分。
有人会认为,那么,是不是我们引入常识(common sense),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日常太脆弱了。
我们知道,基于 common sense 的某些哲学家会强调:“我就是知道……”——关于这一点,我前面其实也说过了,“我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想把它作为一个绝对的规律,那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些瑕疵。”考虑如下攻击:
纯粹经验主义者:筷子看上去是弯的,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直的。
常识主义者:通过常识我们当然知道筷子只是看起来弯的,它当然是直的!
——结果后者被整蛊了,真的有人准备了一根确实在水面处弯了的筷子。
同理,我们可以构建打光苹果的 case:
纯粹经验主义者:这个苹果看上去是黑色的,我们不知道它在正常光照下是不是红色的。
常识主义者:虽然这个苹果看上去是黑的(在绿光下),但是实际上它是红色的。
——结果真的是一个黑色的苹果。
笑死。
当然这些整蛊都只是用来一击脱离,除非有魔术师的参与,否则几乎没法作为针对“转过头不看”或者“屋子里关灯之后乌漆嘛黑什么都看不到”的情况的攻击。
这个地方要怎么构成一个哲学问题?
我们似乎在怀疑这样一种可能性:有一个恶趣味的邪神,或者说魔鬼,在和我们开玩笑,苹果只有在我们,又或者,你干脆用一个唯我论的视角来说好了,只有在我看到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当我看不到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从游戏的角度上来说还真有可能。如果你是一个游戏玩家,电脑上在跑一个大型游戏,显卡对于那些远远超过视角范围内的对象可以不用渲染,节省算力。笑死。——事实上没有什么办法去打破这种唯我论的迷梦。我的意思是,对于一个唯我论者来说,连我这个目前正在写文章的人都是一个不必存在的东西。反正他只要没见到我,那我就不存在,这个答案看上去像是我写的,但是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就像是游戏里面 A 给 B 写了一封信,你作为玩家看到了,你不会真的认为是那个 NPC 拥有人工智能给 B 写了一封信,对吧。
笑死。
又或者,回到上面那个针对常识的整蛊。
如果你看着这个苹果,可能布一挡,一撤,呀!它变成了一个青苹果,然后布又一挡,又一撤,诶!怎么变回红苹果了!——你看,这里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从日常的,看破魔术的理解来说,当然是魔术师换了苹果,我根本不怀疑苹果的“第二性”,我们怀疑的是苹果的同一性。——哪怕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也不会相信“变色”这种表述,而只会考虑“肯定是苹果让他换了”这种可能性。
但是,即便不是魔术,而是真正的魔法,那又怎么样呢?我们会说,魔法师通过咒语改变了苹果的颜色——对,我们不相信苹果自己会变色,我们得要一个原因。
我们只能装成是一个能力有限唯我论者,而没有办法,或者说,很难想象成自己是一个绝对的、无限的、控制一切的我,因为我不是上帝。我能够感受到一种局限性。就像是游戏,游戏里面虽然我就是上帝,但是我也不是在游戏里面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开发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上帝,我受到开发者设定的那些东西约束。而开发者自己当然也不是上帝,他们受到产品经理的约束,受到投资人的约束,受到申鹤的约束,受到编程语言规范的约束,受到小组内代码规范的约束。
上帝可以是一个“完满的”唯我论者,祂说有光,就有光,但是“说”只是一种隐喻,祂需要说吗?祂想有光,就有光。对于祂来说,intuition 和 concept 是合一的,我们的 sensibility 是一种 receptivity,是被动的,但是祂不是。
对于我们来说,law 必须要存在,不管你这个 law 是 natural law 还是别的什么 law,为什么?因为你面前的东西,不管是我写的文字还是你看到的屏幕,不是你想不看到就能不看到的。你得做出合乎物理规律,或者说,合乎日常经验(这不是说 perceptual experience,而是类似于“我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喝到水”经验知识)的操作才能让它们不见,比如说,你可以闭上眼睛,关掉窗口,切换程序,把手机放到一边,或者扭头。对于我们这些无能的人类来说,law 是限制,也是工具。工具本身就同时是 limitation 和 empowerment。工具只有按照合乎特定方式的方式使用才是工具。这不是说我们不能把砖头当锤子用,但是我们没法把豆腐当锤子用——为什么?弗里德里希·你猜。
回过头来,当然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些凡人没有办法理解上帝,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想”本身也是一种 action。全能也要以正确的方式运用能力。哪怕我是上帝,我想要有光,我也得想光,而不是想暗。——我不是说上帝如何如何,我当然不知道上帝如何如何,而是说,你看,这种“受限”其实植根于人类的思维模式之中。我们是如此地受限。
这就让我想起了那个我反复讲过很多次的 Anscombe 的笑话了:
你说你可以举起手,而不能举起这个火柴盒——荒谬,举起火柴盒就和举手一样,轻而易举。但是,如果你说的是,你不能用‘火柴盒火柴盒起来吧’这样念咒语的方式举起一个火柴盒——那么在相同的意义上,你也不能举起自己的手。
而为什么物体(在一定限度内)不会变色?这当然是我们的信心和假设,我无法回答一个唯我论者的质疑,因为对于他来说根本没有我。但是哪怕是一个唯我论者,我们也看到了,我们需要用某种“规律”去限制,比如说,用所谓的游戏的隐喻去限制,而虽然日常规律破产了,但是游戏内部的设定又变成了一个新的规律。这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the need for laws is undisputed。除非你真的是上帝,你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否则,你还是得被各种条条框框约束,你哪怕是为了和 NPC 说话,你都得选“正确”的选项。——对,我心灵不存在,这篇文章全都是 AI 自动生成的,没有任何和你同等地位的“人”想要说服你——那又怎么样呢?你以为的“语言规则”,哪怕你当它是和 NPC 互动的规则,你都得遵守它,否则我们这些 NPC 也不鸟你啊。——大概这种感觉。
日常意义上来说,一方面,我们假定了物理规律具有某种齐一性,而另一方面,则是在不违反物理规律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假定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故意整蛊你的东西,而更进一步,哪怕是非日常的情况,但凡我们还要谈论一丁点的理解,我们都得假定某些东西。
这些东西虽然是“假定”是可以质疑的,但是除非你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故事,否则我没有理由在意你,但是你的更好的故事是什么呢?另一个假定。
当然了,这里已经超越了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分野,又或者这样说,所谓的“假定”其实弥漫于科学中,虽然说 manifest image 和 scientific image 的区别,其实前者完全没有任何“不科学”的味道,如果只是接受科学方法论和经验统计的话,没有问题,但是只有后者的图景中才会有那些理论假定的实体。而这个界线也不是死的,在看不到基因的时候,基因是理论假设实体,属于后者,但是当我们能抓 DNA 来进行基因测序的时候,基因就不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理论实体了,它属于前者。古代我们无法操控电力,把它当成怪力乱神的玩意儿,现在我们知道电是什么,所以“电”变成了 manifest image 的一部分。
这不是说“假设”都可以一概而论,只不过是想说,你看,实际上所谓的假设真的遍地都是。试图想用某种 scientific image 来说我们“不需要”假设,其实根本就是缘木求鱼。原子分子姑且都是 manifest image 里面的东西了,但是弦论或者更加 fancy 的当代物理学理论里面的那堆玩意儿,则又依旧是假设的理论实体。fictionalism 的问题恰恰不在于感觉、数字、道德、价值、桌子这些东西是虚构的,而在于,为什么物理学概念,尤其是最前沿的那些,不是虚构的。怀疑论的刀砍下去是收不住的,但是怀疑论本身在行动上又不够自洽:可以问一些问题,但是你不能一直问下去,毕竟,看上去的对话者,比如说我,或许根本不存在呢?你在讨论?和谁讨论?有人吗?——当然,这个时候奥本海默剃刀就有用了:我剃掉你这个问题!